书评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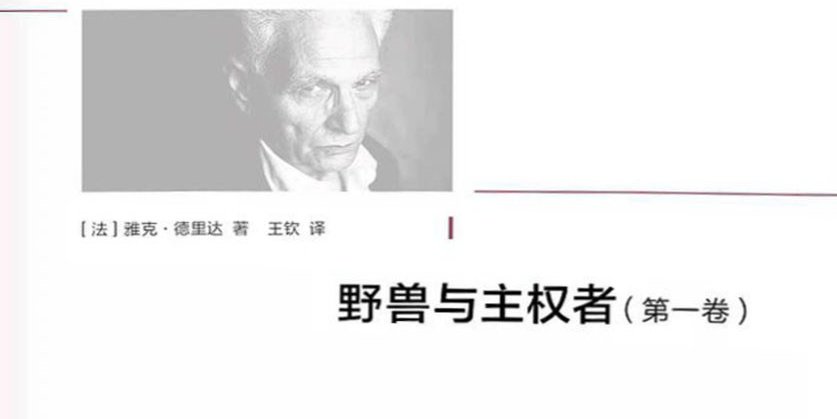
雅克·德里达,《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中文译本于2021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王钦.
“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黑格尔 《美学》
“‘我们马上会显示这一点’(板书)”——德里达 《野兽与主权者》
虽然《野兽与主权者》的法文版编者在“编者说明”中做了如下解释:“如‘(板书)’、‘(朗读并评论)’、‘(重读)’、‘(发挥)’——它们为研讨班赋予一种节奏,带来重音和抑扬”,但我们知道,在关于德里达的解释中,即便只是这种无关紧要的技术性细节,将“文字”与“声音”不加区别地并置也不可能令人满意。“(板书)”,这个注解符号在课程的一开始就提醒读者回想“语音中心主义”错觉,并以此作为开端。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将这一错觉揭示为语音对符号中介的无感,这意味着在语音中“能指”被消除了,“真理”于是在这种错觉中脱离了任何中介系统。这一错觉所掩盖的正是“差异”,这一属于“书写”的交流条件的预先奠基。文字或者书写,它是一种人造系统,但它并非某种“第二性”的人造系统,而是关于“人造”自身的预示。然而,“(板书)”,编者声称这是一个拍号,暧昧地表达了这一双重性:它是读者手中的这部《野兽与主权者》里的一个对阅读施加影响的标识,同时又表明了纪实性。就后者而言,不是“(转身写)”——真正的纪实,一个动作,而是“(板书)”——接下来这句话又被揭示为引文。“马上”,想象一下这个词的运用场景,一种顷刻的落实,自我命令式的语旨力溢出……
让我们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马上会显示这一点’(板书)”,这到底是一段语音还是一段文字?德里达的整个课程几乎就是在解释这个开篇被提出的“谜面”,虽然这也许是和编者的偶然合谋。当德里达承认这句在研讨班进行期间不断浮现的话是一段引文的时候(引自拉伯雷,但也仅此而已),他几乎承认了它是一段“语音”,但它正是在“书写”中才成为了一段“语音”:想象我们走进这间教室,面对黑板上没有擦掉的这句话,就像科幻电影中在外星面对未知文明宏伟遗迹的探索者,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并且它已经结束了,它已经“显现了”(一种完成态,尽管字面上是将来时)自己。但是,过去某一个时间点的“马上”,一个无限短的将来时修辞,我们就被囚禁于此:只有在显现前无限短的尚未显现的时间里,我们才能把握这一显现。
想象一个研讨班如此开场,蹑手蹑脚/以狼的脚步:
“我们马上就会显示这一点。”什么?我们马上就要显示什么?没错,“我们马上就会显示这一点”。
想象一个研讨班以“‘我们马上就会显示这一点。’‘什么?我们马上要显示什么?’没错,‘我们马上就会显示这一点’”开场。这几乎什么都没说。
此处,德里达展现了一种“空转”。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空转”不同,这一空转不是“同义反复”造成的“空义“(nonsense),仿佛一种原地踏步。它显然有些许挪移,并且能够被字面地看出递进。而整个研讨班就在这种“空转”中“蹑手蹑脚/以狼的脚步”般地展开,并由此引入关于“野兽”的讨论。德里达实际上在敦促听众设想“遭遇野兽”这一经验,而非“对象-野兽”这个范畴,期间我们发现了自己对“野兽”这一对象认识中的矛盾。“野兽”,关联着这样一些谓词:狂吼、吞食、冲击或碾压,在“狼吞虎咽”这个成语中我们正是如是设想。但通过在“遭遇野兽”这件事情里掺入恐惧的体验,德里达让我们看到,“野兽”恰是被其所“不是”预示了它的来临:沉默、蹑手蹑脚,“以缺席的方式提到了狼”。“野兽”,无论它到底是不是“对象-野兽”,它存在于“埋伏”和“无状”之中。想象被摸到了不适的位置而突然挠破人胳膊的猫,或者突然在眼前振翅而飞的鸽子,它们何以以非“对象-野兽”这一的形态而“马上显示”为与惊恐相关涉的“野兽”。

上述“无限趋近”与“动物”相关的论述在德里达的著作里出现过不止一次。在《我所是的动物》(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2006)中,德里达讨论了与猫赤裸相对的体验,他将这一体验表述为对自身“动物性”的追逐。这种追逐在传统哲学中被赋予了一个目的地,人们到达“动物性”的底面,并在此基础上制造自己的“人性”。人与动物的界线之所以能够被划定,是因为人将自己理解为对“非人”的克服或者逆转。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永远处于这一追逐之中,并也因此在“对象-人”与“非人”之间无限小的界限中成为“人”(“我们马上就要显示人” [裸猫-裸人])。
对于这个“谜面”的破解有助于我们破除对于德里达思想的一个误解,即他对“XX中心主义”的批判意味着他反对某一方而支持另一方。德里达真正的立场是,语音与文字、人与动物,乃至家畜与野兽,它们并不在一种排斥性关系中被认识,而是处于一个普遍的符号区域。虽然在我们提出的所有对象性问题中,这一区域只是一个几乎不可见的缝隙(“马上显现”,“立刻决定”,仿佛一种依赖决定论积累的生活幻觉),但我们就身在这一缝隙中。
而缝隙两边的差异是决定性的,从“我们马上就要显示这一点”到“它确实被显示”,相当于进入德里达所谓的“制造知识”(faire savoir)的过程。按照德里达在课程中的举例,现代媒体在危机报道中运用“档案的可复制性”,制造了一种关于危机的“知识”。
此处,我们必须将“档案可复制性”区别于本雅明关于艺术作品的“机器可复制性”。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往往被忽视的一点是,本雅明在“原作”与“机器复制”两个艺术生产阶段之间单列出了一个被称为“赝制”(forgery,即以追逐原作为指向来制作赝品)的阶段,这一段落相当不起眼,但它却标明了人工技艺朝向艺术本真性的一面:在对于原作无法达成的追逐中,人工技艺“马上就要显示这一艺术”。用本雅明的话说,“赝制”证实了“原作”的“权成”,正是因为它试图无限趋近原作却又永远被斥为赝品,它与原作之间才形成了一个关于艺术品的普遍符号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我们说“这很艺术”,而不必强迫自己做“这是艺术”的断言,这正是德里达所主张的有“值得被称为知识”的知识存在的区域。
机器的“可复制性”作为“赝制”的下一阶段,实际上被本雅明表明为上一阶段的自然扩展。对立于这种自然拓展,德里达指出了一种存粹的“人工制造”,并使用了“假肢” (一种“伪手工”)这一意象。主权,在德里达的课程中被表述为“假肢-国家性”,这一机制的实质是强制弥合那道至关重要的缝隙,关闭这个普遍符号的区域。在这一机制下,事实上发生的即“强迫知道”,或者结合野兽的意象来说,这一机制令我们“强迫进食”,正如假牙让某个年龄段的人能够进食实际上已经无法被肠胃消化的食物(从这个角度看,肢体与消化系统及脏器的协同衰老是一种良性机制)。“假肢-国家性”所承诺的“保护性”,就是通过“显现”危险之是,“显现”野兽之所在而实现的。它并不真的阻止野兽的出没,是仅仅是一种野兽“显现”的畅通无阻,或者说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的无中介化,一种危机的“形而上学化”。
如果我们能够思考德里达与本雅明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我们就会自然想到在本雅明笔下,弥赛亚也是以其缺席显现自身的。从窄门“侧身而入”,何等的“蹑手蹑脚”,如同德里达所说的狼。此处,我们可按照社会契约论里描述前政治(自然)状态的著名论断“人对人是狼”制造一个与之字面同构但向度完全相反的命题:“弥赛亚对人是狼”。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将本雅明的弥赛亚解释为“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它对立于“主权者”,让符号的“普遍区域”降临。它不消除任何“差异”,而是持存“差异”的预表,让事物在差异甚至对立的杂多中透显,故而在《无信仰的信仰》(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2012)中,克里奇利称之为“神圣暴力的非暴力性”。反之,根据德里达在“野兽与主权者”这一表述中对阴阳两性的反复提及所暗示的,“人对人是狼”则作为“假肢-国家性”的一个衍生命题。根据德里达的“谜面”,这一命题所实际主张的是每个人需要在他者的缺席中认识他者,于是人们以“假肢”——契约、律法或任何主权者媒介——欣然相会:“‘我们马上会显示这一点’,‘好的,我知道(看到)了’”。
在较短的篇幅里对德里达的讲座文案做全面的评述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对“谜面”的分析仍然能够给出一个德里达基本思路的引导,并且确实在《野兽与主权者》这样的讲稿中,德里达的表述和延展都比他的著作更清晰。通过缺席甚至相反者显现在者,这一形式逻辑改造始于黑格尔。“一切事物自身都内在的矛盾”或“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在相当广义的意义上可以将之视为解构主义的先导,或者以某种激进的视角视解构主义为黑格尔哲学的当代版本。这一“当代性”是由一个微妙的偏移造就的:如果说在黑格尔处,事物自在于“示其矛盾所是”,那么它的当代版本则是一种“示其非所是”,它拒绝“示其矛盾所是”向“示其所是”在观念上的无碍转化——“假肢-国家性”即为这种转化提供便利。德里达、柄谷行人、拉康与齐泽克都属于这一黑格尔主义的当代版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以“示其所是”为宗旨的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很多知名的阐释者那里,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更亲近黑格尔,而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则保持着对德里达的商榷立场。
德里达实际上“拾起”的正是黑格尔在建立其形式逻辑伊始所摒弃的一个中间阶段,即“具有”(Haben),而非黑格尔所意求达到的“是”(Sein)。因此,“我们马上就要显示这一点”,“理性马上就要显示为这一感性”,这一改造实际上开辟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人类学”区域,即一种不可抹除的人类所“具有”的“趋势性”的知识论,这在德里达看来才是值得被称为“知识”的知识。《野兽与主权者》落实了德里达的上述思想原则,并实际上诱导读者进行这样基于这一课程开篇“谜面”的改造:只要我们思考一下“存在即合理”基于“谜面”的改造版本:“我们(的存在)马上就要显示其(具有)的合理性了”,两者在政治学上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林云柯,文艺学博士,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
文/ 林云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