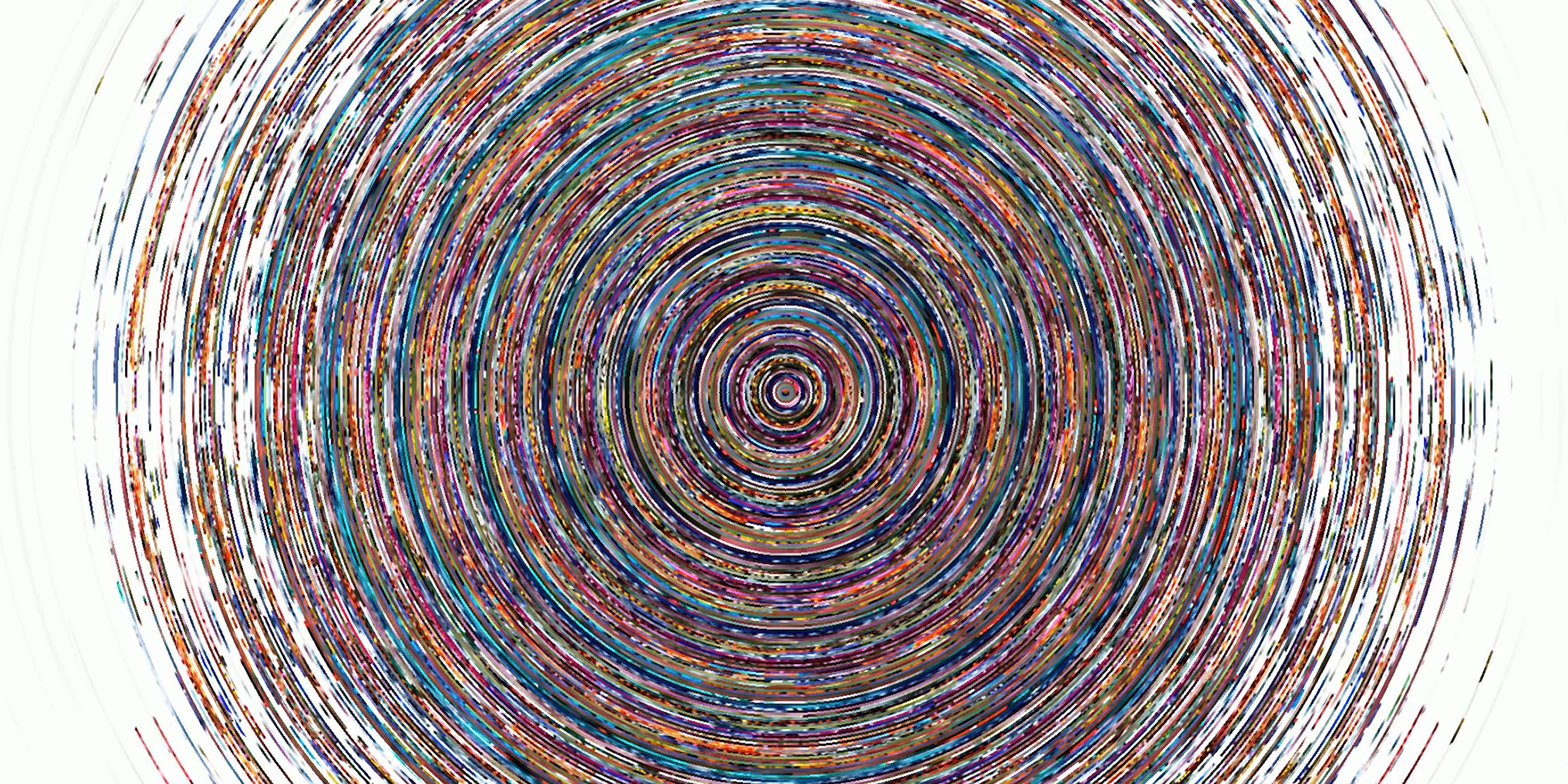吴厚挺
从2017年起,吴厚挺开始将日用消费品包装箱内部填充物与商品之间形成的“间隙”转化为三维实体。他在东画廊的最新个展“2066”中展出的十五件形态怪异且带有未来感的雕塑作品便都取型于“商品外部造型结构、包装箱内防震、减震的塑料泡沫块形态以及存在并充斥于这两者之间的间隙空间”。
这是由技术残留物构成的空间。存在于物与物之间的间隙更是凸显了残留物本身的去价值化状态——它们仅仅是系统内部的一种临时性功能,是无用的、不合常规的、本应消失的状态。同样,我们也可以将其解读或想象为有关人类未来处境的某种隐喻:加速发展的技术正一点一点地剥除人类原有的能力与特质,瓦解其主体性,令其沦为技术的“残留物”。
吴厚挺将这些雕塑作品分散放置于竖直的矩形或梯形基座上,使其如纪念碑林一般屹立在展厅之中,在这里,技术的残留物占据了主导位置。而对于必须面对类似命运的普通人而言,价值的丧失并非例外,而是常态。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视各种被边缘化的、被剥夺意义的群体,保存作为残留物的共情能力,在此基础上,尝试撰写一种基于残留物立场的历史,以之照见自身的处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吴厚挺的雕塑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是从该立场出发撰写的一种未发先至的历史。在他的叙事中,残留物形成的共同体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一种被命名为“破格”,另一种则是“弦”。在“破格”系列中,艺术家根据物与物之间的空间形态和尺寸来寻找某种恰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