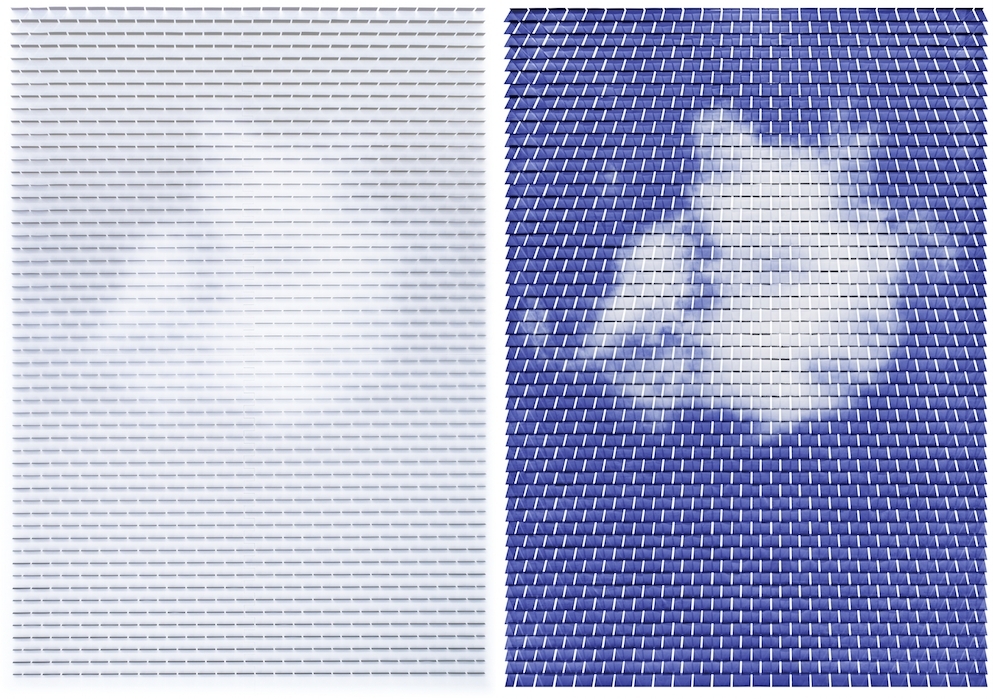崔洁:新旧都市方案
“新旧都市方案”的标题灵感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活跃于日本建筑界的“新陈代谢”派,该流派强调城市的有机生长和自然进化。虽说灵感源和画面内容皆为建筑,但崔洁的作品不止于建筑图示;画面虽然抹掉了人的痕迹,却透露出由建筑和城市规划所激发出的人的情怀——在这种情怀中,对过往的留恋与对当下的恐惧并存,唯独没有未来。
此次展出画作里出现的建筑物原型最早出现于上世纪末第一批大规模城市规划热潮,如今在任何一个一线城市外围或二三线城市中都随处可见。在九幅油画中,一座无名的高楼反复出现,其边棱往上延伸出一个环形瞭望台。它在一些画中是主角,在另一些中则是远处背景里的一个小黑影。楼房与雕塑互相镶嵌,两者结合,形成某种建筑怪物。雕塑的形象也是我们在街角路边最常见的:鸽子、仙鹤、抽象的飞舞缎带、被托起的不锈钢圆球等等—都是经中国现代主义诠释的公共艺术典范。与楼房等大、且彼此纠缠在一起的仙鹤看上去酷似恐龙,使我们分不清画中场景究竟是史前世界还是已被人类文明消殆尽的地球末日。在崔洁的作品里,这些结构显得理所当然,就像过于真实的幻境,不知是在质问还是在维护现代主义的黄粱美梦。
对集体无意识的探讨与对绘画本体的追诉凝聚在同一系列动作里。画布上层层覆盖的颜料让人联想到“建造”这一行为,不同涂层代表了不同平面、纹理或物体。从展示的手稿中我们仅见到简单的形象塑造,最终完成的作品却层次丰富,由此可以想见,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