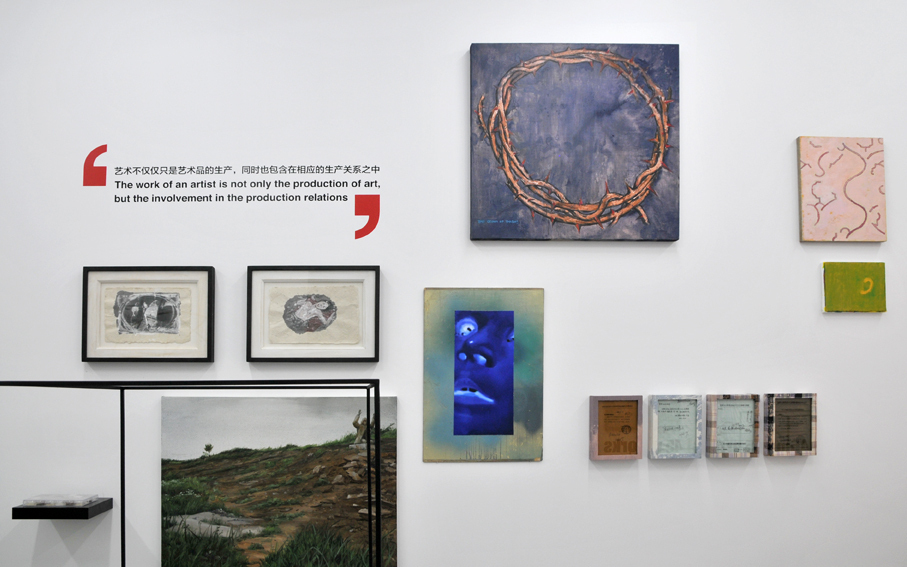身份与地方
于2000年在雅加达成立的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自2019年起担任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总监而备受瞩目。虽然该团体近年来媒体曝光甚多,但是由于疫情所导致的国际交通停滞等因素,他们的筹备工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也一直面临着很多争议。本次访谈邀请了曾于2018年访问广州和深圳的ruangrupa成员farid rakun,从近年来艺术界所关注的身份政治和地缘政治议题出发,结合他自身的求学和家庭经历,谈及ruangrupa近年来的工作心得,包括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主题“米仓”,如何选择合作对象,卡塞尔做为一个地方概念,“南南合作”的困难等等。
对于ruangrupa来说,他们想要挑战艺术界流行的“东南亚”或“亚洲”等基于地理和族裔身份的认知框架,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以脚下的土地为据点,把地方实践做为方法,去破除对于西方机构的迷信,包括何为“艺术”的定义,如何“展示”艺术等等。这个理念或许相当理想化,并非被所有人所认可,也非一届文献展所能达成。笔者自2016年起接触ruangrupa并在不同场合与其相处共事,对此深有同感。目前的全球疫情无疑对此类强调在地的实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为本届文献展的最终呈现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我们不是基于地理分布去选择合作对象的。这不是奥运会。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对于基于世界地理的思路表示怀疑和批判。对我们来说,当身份成为一些更具体的指向时,比如性少数群体,受压迫群体,边缘化群体,原住民,美国黑人,哥伦比亚人,丹麦的寻求庇护者(位于丹麦的米仓成员Trampo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