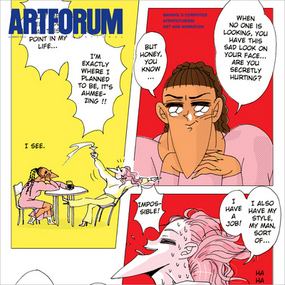我们不能期待画出大师级作品。我们也许只能满足于到颜料盒里做一次愉快的兜风。而要获得后者的入场券,只需大胆而已。
-温斯顿・丘吉尔,《绘画作为一种消遣》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退休长跑冠军Metro Meteor转型成为画家的报道。Metro Meteor作画时,助手会在画笔上绑上胶带,以免他用嘴咬住笔时不会碎。为了防止串色,他每天只画一种颜色。据推测,他是凭感觉作画的——毕竟,身为一匹马,他的眼睛长在脑袋两侧。
我说起Meteor并不是要把他的作品跟另一位更著名的退休后转型艺术家的创作相提并论,而是为了框定一个问题:对于圈外人,绘画是高雅艺术的象征;对于业余爱好者,绘画是最平民、最具诱惑力的消遣;身兼上述两种身份的绘画很容易变味,尤其是在媒体报道里。从乔治・W・布什决心要认真画画的那一刻开始,这事儿就注定会成为全球新闻的一个焦点。
看它引发了多大的一场新闻风暴。世界各地评论员的行动让人充分看到新闻界自身以及我们所处的整个文化如何努力地想要搞明白或说清楚这位对进入2000年以来的世界图景造成了决定性影响的总统。很多文章说布什画得笨,或者考虑到“战争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干脆直接说他画得惨不忍睹。英国一篇奇葩文章还拿他跟丘吉尔作比,说后者从绘画里得到的乐趣至少是“他自己挣回来的。”另一些评论家从中看出布什想用平民风格挽救自身形象的可怕阴谋。其他则指出布什所有源图像都来自谷歌搜索这一事实导致他的整个实践无法成立,或者从整体上攻击现成照片的使用本身。还有部分评论家为画作辩护,认为其颇得纯真原始之妙趣。但也许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谐星们纷纷拿此事开涮,互联网上也是疯评疯转不止。我也是普金画像刚一放出来就把图发给了一个朋友(朋友回信:“Dana Schutz的画??”)。当我登上去达拉斯的飞机,准备去看在乔治・W・布什总统中心举办的展览“领导的艺术:一位总统的私人外交”时,好奇心止不住地飙升:终于要跟网络红人作品面对面了。
跟图片比起来,真画既更有趣,也更无趣。我去之前对画面是如何搭建的有一些设想,比如普京难看的凹脸颊,默克尔眼下发白的眼袋看上去都像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一开始在某个局部花了太多笔墨和功夫,想起来了才火急火燎地去完成其他部分。但这些画经过复制后看上去比原作显得更加潦草,漏洞百出。哪怕是简单的绘画,实际看到作者如何通过双手思考也会改进我们对作品的体验,此处也的确有不少看点,即便很多都是在美院一年级习作里常见的问题(实际上我正好兼职在教一年级的课)。画得生硬;耳朵部分特别造成问题,而下巴跟颈部的过渡连接则几乎没有。同时,画面中也不乏明显的赏心悦目之处:阿卜杜拉国王的绿眼镜堪称神来之笔,某个撅起的嘴唇或鼻子后面扭曲的褶皱颇见功力。布什画作的表面平滑顺畅,颜料用得自在自如,有时在画面上留下指印,有时就像我们在他自画像脸颊部分看到的那样使用一些佩顿式的透明过渡。
当然,也有进行得不那么顺利的地方,但旧货店里无名业余画家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硬生生的紧张却没有。与网上疯转的那批诡异的浴室画不同,布什这些直白的肖像画里一点儿都看不到“天真艺术”的无知无畏,但也没有像Jim Shaw那种故意模仿里的自我意识。如果你是在切尔西某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看到这些画,你也许会把其中的粗糙看成艺术家的自信,而其中的意图则反映了某种时髦。在后现代-巴洛克风格的总统中心——墙上的壁画式照片上,劳拉・布什穿着红缎裙牵着狗坐在白宫草地上——这些画显得出奇的直截了当。
换句话说,说到底一切都是个语境问题。前总统先生觉得自己是画家,但我们是不是把他看作一名艺术家?丘吉尔在谈论自身艺术实践的著名文章(正是这篇文章激发了布什的艺术热情)里诡异地将军事布署和户外绘画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也提到第一次拿起画笔是在自己政治生涯极端受挫的时候,即当他被挤出海军部的那段时间。其他人在布什的新嗜好里看到了逃避或自我治疗,但这里面还有丘吉尔所谓的“消遣”在,自我改进和自我反思在后者暧昧的概念里跟快乐地消磨时间混杂在一起。如今,部分批评家开始探讨艺术的治疗功用,包括简单的放松——比如,苏珊·哈德森(Suzanne Hudson)就对鲍勃・罗斯的招牌节目《绘画的快乐》里那些不画画的观众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也许要真正理解布什的作品,我们必须(满心紧张地)去处理一个问题:绘画这一媒介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到底代表着什么。大伙儿都爱它。而这一点让我们当中一部分人掉进了批评的无底洞。因此,对我而言,把布什的新嗜好定性为邪恶真的很难,我甚至想进一步说,布什的绘画也许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的谜题,至少从最初的冲动来说是如此。
“等我上了天堂,”丘吉尔写道,“我想把第一个一百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画画。”无论是为了消遣,赎罪,还是为了最后的奖赏,布什人生倒数第二站似乎定在了达拉斯的一间休息室,而他的声明并不平淡,也不该被“错误地低估”(译注:misunderestimated,布什自己发明的新词):“我会一直画到死。在我进入坟墓之前……这最后一笔,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颜色?”
马特・桑德斯(Matt Saunders)是一名艺术家,现居柏林和剑桥(马萨诸塞州)两地。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