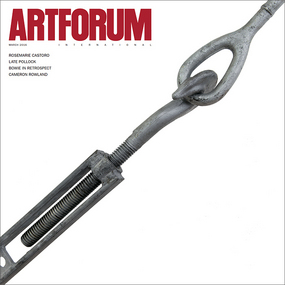82岁的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Álvaro Siza)迄今已经完成过约400个各式规模和形态的建筑作品,他或许是目前仅存的一位仍以在战争期间驱动了整个欧洲前卫艺术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己任的现代主义大师。西扎在事业伊始是一位住宅建筑师,他的建筑师生涯的前十个年头都是在设计一些私人房屋,但很快他就开始投身“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运动——这是安东尼奥·萨拉查(António Salazar)长达40年的独裁政府被彻底推翻后,葡萄牙于1974年4月经历的所谓葡萄牙之春(Portuguese Spring)高涨的乐观主义带来的关于社会住宅的典型的现代主义类型学。西扎的项目集中在波尔图(Porto),在SAAL(Serviço Ambulatório de Apoio Local——地方流动支持站)的赞助下展开,该组织在社会主义临时政府支持下于1974年的革命余波中创建。它的目标是改善葡萄牙城市中的住房状况,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思考建筑的社会角色,以此解决葡萄牙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在SAAL的实验性模式下——艺术史学家苏珊娜•克特(Suzanne Cotter)曾经协助策划了2014年在波尔图的塞拉维斯当代美术馆(Museu de Arte Contemporânea de Serralves)举办的关于该组织的百科全书式的展览,她将这种模式描述为“20世纪建筑学中最激动人心的尝试之一”——建筑师会和当地社群一起探讨住宅的形态。不同于大部分战后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那种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兴建方式,这些未来的住户将亲自参与楼房的建造。
这些参与性项目中首个成果是位于圣维克托(São Victor)和博萨(Bouça)的住宅区——由西扎在1974年到1977年间设计建造的一些十分出色的低层住宅。但这种多方参与的设计绝非一个轻松的过程,就像西扎本人在评价工人组织和SAAL建筑师之间的合作时所说:
“他们的态度有时非常专横,他们会完全否定建筑师考虑的问题,他们会把他们看待和思考事物的方式强加在你身上……真正进入参与的过程意味着你必须接受这些冲突而不是隐藏它们,相反,你应该想办法去进一步展开探讨。这样的交流尽管艰难甚至痛苦,却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成果。”1
圣维克托的排屋住宅区是一种两层的建筑,建造在一片部分严重损毁的废弃排屋群中。西扎似乎将这个项目想象成了一种对古代遗迹的修复——并以此建立起了他此后长期的工作方法,不仅在他的设计中囊括进地貌的肌理,也将该地的历史和过往的文化考虑在内。
SAAL的第二个项目,位于博萨的住宅区,是一片梯形的建筑群,该区域内原本的建筑都已被拆除。这个住宅区最长一条边是一堵四层楼高的砖墙,用来挡住临近一条铁路线的噪音。整个结构包括四排平行的四层楼高的不同内部单元结构的连栋楼。在其中一些建筑里,最高的楼层由外部独立阶梯直接连接到地面,通向不同区块间的前院。较低层的单元则共享一侧配有楼梯的非封闭式过道。而在每个单元内,内部楼梯的位置安排让住户可以自行选择哪个空间最适合日常活动,哪些更适合充当休息空间;这些不同的方案来自建筑师和未来住户之间持续进行的讨论协商。因为场地形状的不同,这些连栋楼的长短不一,最后汇集在那堵防噪音墙,而在另一端,则是一栋小型的转角楼(batiment d’angle),可用作公共设施,诸如洗衣房、图书馆或是便利店。这些公共设施的提案也反映了西扎对于该项目社会性的关注和投入;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最终都没能实施,而这第一点也反映出了SAAL系统的局限性。1975年,右翼发动政变之后,SAAL的权力已经全面瓦解,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整个参与性实践也归于沉寂。
尽管西扎的下一个项目并不是在SAAL的支持下开展,但他仍然在自己的工作中引入了不少参与性项目的特点。博萨的项目之后不久,西扎就开始为一个名为马拉古埃拉堡(Quinta da Malagueira)的区域设计一些低楼层、高密度的住房,这个区就坐落在埃武拉区的阿连特茹城外(the Alentejo city of Évora)。西扎接手的这个项目是要在一个已经布满了自建房屋和一些兴建于1960年代的中层社会住宅的区域内新建造1200个住宅单元。就像是在博萨,他把战争期间魏玛共和国的那些社会住宅作为构成和布局方式的范本,尽管他设计的单个住宅单元都非常不同。他选择了一种两层的构造,用一个L形的院墙把房子和街道隔开。这个项目在马拉古埃拉政府的支持下持续进行了20年时间,实际上马拉古埃拉住宅区是对一直以来地中海城市常见的那种低层、白墙的传统建筑的再加工,你甚至可以说两者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西扎对于门窗密度和比例的改造,这种设计方案看起来像是取自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偏爱的那种绝对抽象风格——这一点或许最为忠诚地体现在了他1923年在威尼斯丽都设计建造的亚历山大·摩伊斯(Alexander Moissi)住宅上。

西扎在他的设计中用到的一个不太寻常的方法是把管道架在没上色的水泥墩上,看起来像是穿越了马拉古埃拉住宅片区斜坡的一座高架桥,这给人一种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遗迹之感。这个集体性的形式不仅提高了生活和维修所需的煤气、电力和其他能源的供给效率,也把单独的住宅单元连接了起来——无论是从实际还是寓意上来讲,所以它大概可以被视作对于该社区未能修建公共设施的缺憾的一种超现实补偿。也是在这个区域,西扎构想了一些未能完成的社区公共建筑,他把失败原因归结为埃武拉区共产党政府和里斯本反动保守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有矛盾。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拨款只能用来修建住宅房屋,但不能用来建造集体设施。直到今天,这个住宅区里也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2尽管存在种种局限,马拉古埃拉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它在解决附近区域停车问题方面的能力,这点在这个项目开始之时并没有被视作必要——这也说明了,专门规划出的社区公共空间并不一定是形成一个集体建筑的唯一手段。
西扎和SAAL合作的项目让他受到了柏林公共事务官员的注意,他们邀请他参与了两个连续的竞标,第一个是1979年格尔利茨市疗养院(Görlitzer Bad)的游泳池,另一个是1980年位于柏林附近,当时已经败落的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 district)内所谓的121街区(Block 121)的改建。(关于后一个项目的详细纪录,以及西扎1980年代为海牙所做的住宅设计,目前正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建筑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Architecture]的“街角,街区,社区,城市”[Corner, Block, Neighbourhood, Cities]展上展出)西扎对于后一个项目的基本构想是重建城市肌理,用一个七层高的转角楼来恢复这个街区已经被摧毁的街角。这次他仍然使用了阿道夫·路斯式的极简风格;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只是一个简单的楼体,没有任何的装饰元素,只是用长方形窗户的密度形成的隔断来制造视觉上的节奏。除去波浪式的建筑形态,这栋大楼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甚至不如在它建造时一夜之间出现在楼外立面的匿名涂鸦更吸引目光:颇具讽刺意味的“你好,忧愁”(bonjour tristesse)。西扎拒绝把这个涂鸦擦掉,从此它就成了一直伴随该建筑的绰号。尽管西扎做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个建筑的建造还是处在一种想当然的规划方式之下,缺少特征并且质量不高,不过整体来说它还是和这个城市保持了一种类型学上的关联,外立面涂刷的是柏林经典的黄赭色。鉴于西扎对于都市和本地形态一贯的敏锐和兴趣,他接受柏林这个围合街区的重建项目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它曾经是,甚至从很多层面来讲现在也仍然是,这个城市的普遍构成单元。
这种普遍性的街区类型学也受到了海牙地方议员Adri Duivesteijn的关注,1984年,Duivesteijn邀请他重建海牙的Schilderswijk区。除了街区形态上的类似,Schilderswijk和克罗伊茨贝格区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区域内生活着大量的移民人口,尽管在Schilderswijk,这些移民大多是北非穆斯林。所以在这个案例里,宗教对建筑形态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居民的信仰需要居住空间分隔成男性活动的公共区域和私密的女性空间。西扎的解决方案非常聪明,他用一面移动墙将两个空间隔开,但同时又不影响未来非穆斯林居住者的使用。就像是博萨项目里那些适应性很强的房间布局,这些可移动的区隔也成为了建筑设计作为社会性进程的有力体现,与此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扎在与当地特殊的场地和语境建立关系,以及运用从更抽象的房屋类型中提取的可变通性之间的平衡能力。
的确,西扎使用了这种可变通性的解决方案,但与此同时,也还是在这个街区中保留了一部分荷兰住宅的传统。这个一次性完成的都市更新方案包括两个四层高的半围合式的街区,大部分外墙使用了红砖,窗户则是镶木框的正方形,并配有直接通向街道的台阶——这来自荷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H.P.贝尔拉格(Hendrik Petrus Berlage)1901年的阿姆斯特丹南部发展计划(Amsterdam South development)。建筑有两个进入方式,既可以直接从街道进入,也可以通过通往二楼的楼梯,进入内部充当厨房和起居空间的走廊。此外还有两个较窄的转角楼梯和两个较宽的直梯,用来供三楼和四楼的居民使用。
对外立面这些充满细节并且拼接式的处理方式来自对语境的敏感,尤其是用深红色砖和浅红色砖在最易损耗的一层临街面以及上面三层之间做出区分。米白色砖也用在了两层高的护墙上,处在这个围合街区外侧两条街的交汇处形成的的夹角,也是在这里,另一个街区似乎是从楼底层那些拱形结构里延伸出去——如同用来补偿存在于西扎最初的构想中却未能得以实施的用作社区公共设施的转角楼——无论看起来多么矛盾。这种白砖外立面也用来把为园丁和停车场工作人员提供的单独的房子吸纳进整体结构——主楼上乡村风格的红色砖墙里会掺进一块米白色砖,而在米白色砖墙上也会出现一块红砖。
我把西扎描述成了最后一位现代住宅建筑师,因为住宅建造本身也随着欧洲各国政府自1980年代开始的福利国家政策而逐渐消失。1986年,西扎还在米兰和那不勒斯提出过大规模的中层都市住宅计划,但那时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经开始在全世界盛行;伟大的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实验已经终结。不过,近期全球性的移民危机和发展中国家急速的都市化进程,都再次使得经济型住房短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显著。而寻求解决方案的急迫性又使得西扎在集体建筑设计方面的先锋性实验变得前所未有的深具相关性。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遗产保护研究生院威尔讲座教授。
注释
1. France Vanlaethem,“为了一种审慎的建筑”(Pour une architecture épurée et rigoureuse),《ARQ:建筑/魁北克》,第14期(1983年8月),第18页。
2. Juan Rodriguez and Carlos Seoane编辑,《Siza by Siza》(波瓦-迪尔瓦津/Póvoa de Varzim,葡萄牙,amag出版,2015年),第179页。
文/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 Kenneth Frampton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