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由亚洲当代艺术周(Asia Contemporary Art Week)发起的第五届田野会议“思考计划”(FIELD MEETING: Thinking Projects)在亚洲协会和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天针对“计划”的表演、演讲与讨论。 “Project”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行动之前”,带有协作性、预先设计和拥有特定目标的内涵。从过去两届“表演”(Performance)和“实践”(Practice)的主题延续到今年的 “计划”,田野会议将目光从对过程的关注,转移到对目标设定的考量。对于田野会议这样一个关注亚洲移民社群、亚洲与全球,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年会来说,川普时代中的移民政策,以及国家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情绪的重新抬头无疑从关键上引导了此次论坛的方向。更准确的说,“思考计划”是关于 “抵抗” 和 “治疗”计划的思考 ——— 从被意识形态割裂的美国出发,探讨基于亚洲、行动在全球的艺术家如何抵抗各自所面临的,与当地特殊的身份、历史和现实挂钩的挑战。
田野会议本身的组织结构和实际操作就是一个面对全球流动性和国家界限提出的挑战:几乎每次会议都要应对艺术家在来美签证中出现危机的情况。对“国家界限”和“流动性”的忧虑笼罩着整届论坛。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系的主任Steven Henry Madoff用康德的话点出了汇聚来自异地人士的意义,为这次会议引出了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线索。他说:“待客友好不是一个慈善的行为,而是一种权利。待客友好意味着陌生人在来到新的地方时有不被当成敌人对待的权利。”在想象“主人” 和“客人”,“家园”与“异国”,“标准化的西方”和“异域的亚洲” 这些对立面中,观众看到的是一系列关于地缘政治和挑战历史叙述的展示。
策划人Leeza Ahmady通过与亚洲各地的机构、画廊和个人的关系网络,挑选出二十三位艺术家及从业人员,他们来自北京、香港、台北、柏林、迪拜、卡拉奇、日惹、孟买、多哈、阿拉木图、胡志明市、贝鲁特、比什凯克、莫斯科等地。由于大部分演讲人身份的流动性,他们都能以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来触及会议所针对的问题。田野会议给演讲者一个表达在其居住国不可公开言说的问题的场合;有些参与者通过虚实结合的演讲和以身体为媒体的表演利用了这次“坦白”的机会,另外一些演讲者则选择了一种更保守的方式,以乐观,甚至回避的方式来看待所面对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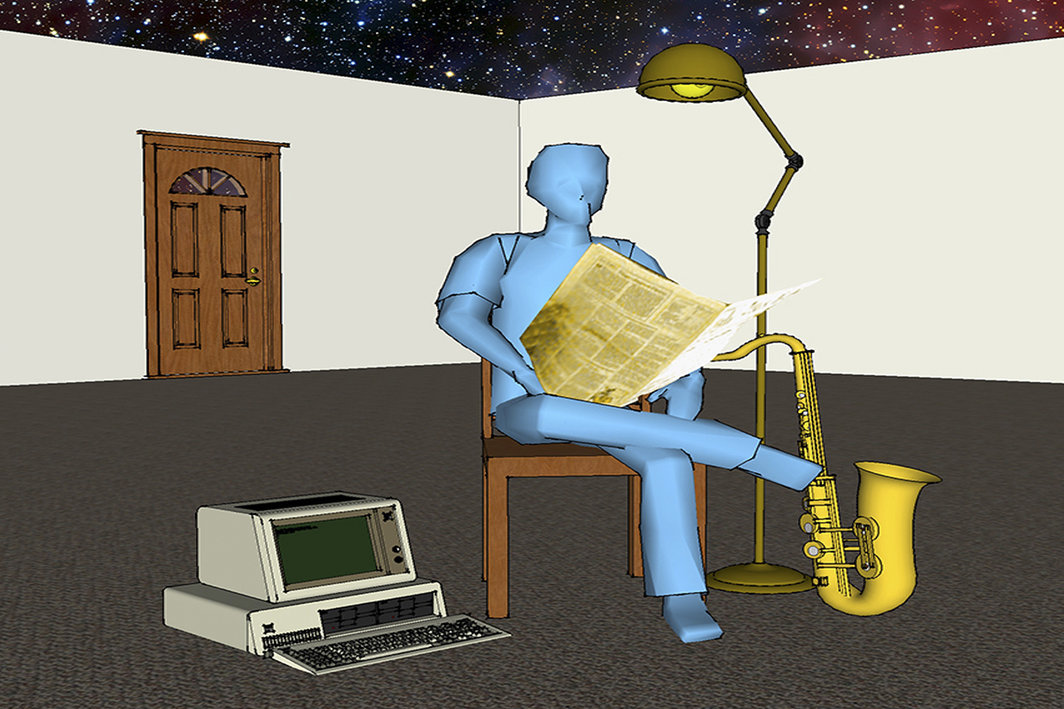
来自日惹的艺术家Nadiah Bamdhaj,生活于胡志明市与休斯顿之间的Tiffany Chung,和在阿联酋长大、目前生活在蒙特利尔的Hajra Waheed的演讲在个人历史和国家叙事之间展开,表现了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被忽略的私人经验,以及个人在不可控历史面前的抵抗。然而历史的叙事是个人想象的结果;也许,尝试更贴切地去呈现它,就是一种抵抗手段。Bamdhaj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的特区—— 日惹王国—— 这个“不言”(unsaid ) 之地的描述突出了建筑空间的集体意义和其可以作为个人内心肖像的双重角色 。演讲中穿插着Bamdhaj在日惹皇宫和皇家墓园等地点与“宫廷成员” (雕塑)和守墓人之间模棱两可的采访对话,最后用哼唱的方式道出苏丹王十世的敛财行为和王国内公共批判机制的缺失。同样以极其个人的视角,Tiffany Chung 透露了她作为难民的记忆和对当下“流离失所”(displacement)现象的思考。演讲在教科书中的历史图片和私人相簿的切换中展开,其中穿插艺术家根据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IDP)的数据编织和手绘而成的地图图像。许多人已经通过Chung在纽约的展览中了解到她对移民问题的研究;这次对大众公开以她父母为例、越战中南越年轻人的梦想与挣扎,是Chung尝试改变这一代人在历史叙述和当代文化中“不存在”的状态所作出的努力。不同于Chung,今年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Hajra Waheed没有设置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引用精确的数据,而是以祈使句为主要句式结构,在叙述中,将观众置入一个“他者” (The Other)的身份当中——这个角色被放逐,被众人离间与指责,被人要求说 “我是个野蛮人”。虽然她并没有说明这个“他者”是谁,我不由得想到了康德口中的那个“有权力不被当成敌人对待”的“陌生人”。
在当前政治环境中,艺术家不免对自己在工作室内的生产感到怀疑;更多的艺术实践采取“计划”的形式来实现干预社会现实的目的。在田野会议中呈现的几组艺术项目把观众带出了针对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极权政治等现实议题的讨论中,用一种相对“另类”的计划来试验艺术在人类精神层面可达到的积极作用。艺术家作为巫师和治愈者的角色在当下继续得到关注。 王浩然(Adrian Wong)讲述了他如何与其他专业人员合作改善展厅或者餐厅的风水,以及在与兔子通灵之后如何为它们建造理想的居所。伍韶劲(Kingsly Ng)运用“城市针灸”的概念,用一系列温柔的公共艺术项目,最小限度地干预来改善城市整体的“气”。艺术表现似乎讲求一种意识形态中的平衡感。在揭开了一块块社会历史伤疤之后,艺术必须给明天留有个盼头。“艺术何为”是人们不断发问的焦点;无论是展览,还是论坛,组织者们在邀请表现负面社会问题的参与者的同时,必须为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即使是象征性的解决方式。带有“治疗”目的的计划提出以传统世界观和宇宙观中的方法为角度,或者说以一个“原始”角度,来面对当下的社会关系和挑战。从组织者的角度来说,这些计划在认清现实之余为集体心理需求提供了一种寄托。作为一个计划本身,它们的“批判性” 在于为批判性艺术提出了一个对立面,呈现另外一种相对乐观和积极的思考方式。虽然它们的作用仍难以避免地更像是一种安慰剂,但安慰剂作为一种在心理层面起作用的处方,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计划。
伍韶劲提出艺术可以作为“一种修复的过程”和“一个聆听的空间”。也许田野会议本身就代表了这样一种过程和空间;在两天之内呈现的艺术计划触及了艺术从感性到研究性、从批判性到治愈性的各种性格,为不同的实践者打开一个聆听和理解的临时场所。在对沉重的话题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保持政治正确的自觉中,我们的疑问超越对“亚洲”和“当代”的纠结,更关心的是艺术在揭开和抚平伤痕这两个动作中的平衡点。

文/ 吕斯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