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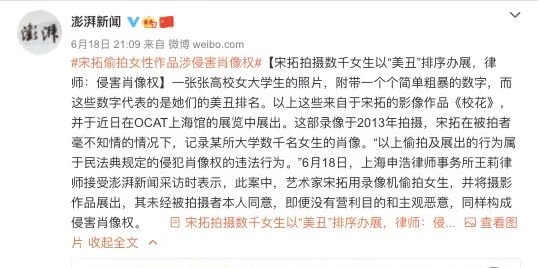
宋拓的影像作品《校花》(2012)于2021年6月在OCAT上海馆展出遭遇的网络抗议及撤展引发了社会最大范围的围观、议论与争端,在近年的当代艺术生态中实属罕见。这一方面反映了性别议题在媒体讨论中的热度和随之引发的公众态度的决定性转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众对当代艺术现场越发高涨的参与度。不过,向来标榜走在时代思潮前沿的当代艺术界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扩大的观众群和社会氛围改变带来的冲击?
事件中的网络热议既包括对这种创作是伤害而不是艺术的严厉质疑,也不乏镜像式的人身攻击和报复性创作提案。这些展厅外的争议最终迫使艺术机构公开致歉并撤展闭馆,而这一过程中,艺术家则处于全面隐身的状态。多家主流文化媒体迅速刊登了立场相异的业内评论:澎湃思想市场题为《冒犯的艺术,谁的同谋》的文章呼吁整个艺术界承担此次事件带来的公众失信,而随机波动与界面文化的两篇评析均强调尊重艺术自由,并呼吁思考撤展以外的其他方案。作为一个社会事件,到此似乎已经终结,但作为一个艺术界的现象,后续讨论却并未真正展开。本文意图以艺术生产和舆论流通的双重视角重访《校花》,通过透析其内部逻辑和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矛盾,提供一种理解该事件的可能路径。
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下《校花》的艺术生产逻辑。艺术家从社会现象中抽取出当前观念下被认为是“小恶”的行为——对他人(女性)外貌进行评判和排序——并在艺术生产的空间中对之进行放大性演绎。对《校花》的一种辩护强调小恶本身不应被封杀,还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反思,但这种辩护显然规避了放大性演绎制造的权力落差。首先,与日常生活中的外貌评判和选美活动不同,艺术家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对数千名女性展开全面而彻底的评判,这一数字上的不成比例反映了作品中评判者与被评判者之间的绝对不平等。其次,七小时影像按排名先后与展厅开放时间绑定放映,相当于把相对中性的公共互动场域转化为与作品内含价值序列同构的临时性状态。艺术家在展厅内如此介绍他的作品:“你想看美女就要起很早去美术馆,反过来到夜幕降临时,这会是一片人间地狱的景象”。换言之,观众踏入展厅之际决定了他/她能看到评分序列中的哪个片断,艺术家预先掌控了观众的部分观看权限。这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令作品及其展示机制呈现出绝对的价值不中立,也就与需要相对搁置价值判断的“反思”行为形成了冲突。
之所以强调价值序列的绝对性,是希望把关注点从艺术家大肆渲染的性别维度转向在大部分讨论中都被忽视的数量级。艺术家在言论中反复征引“物化”、“女权”、“男性凝视”等性别理论关键词,意在用这些愈发具有公共辨识度的语汇激怒、诱导公众。但仔细审视可知,性别内部的权力关系仅是作品中更复杂的权力结构的特殊体现,甚至构成对之的掩护。而当两性间的权力落差被放大数千倍,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对之的强化,亦是对之的普泛化。《校花》中的视觉评判也并非一对一的“男性凝视”,把对象放入数千人的价值序列的基本意图始终蛰伏其中。在争议爆发时被广泛传阅的一篇2019年的采访稿中,采访人邀请艺术家将自己排入五千人名单的桥段生动演绎了这种视觉评判的特殊属性(她收获了277/5000+的名次)——作品中的每个影像片断不是孤立成段,而是内嵌在一个连续且绝对的价值序列里。个体观看者的“质疑”不仅难以撼动其整体结构,还不得不建立在参与其中的前提上。此时如果我们只是对艺术家的性别对立修辞感到愤懑,反而会让他免于这样的诘问:为什么艺术家能同时凌驾于人数众多的被评判者和数量同样可观的观众之上?
《校花》的操作手法在艺术界并非孤例。从表面来看,它把社会现象置换到艺术生产的价值中立空间来激发“反思”,但置换过程中创作者却不对现象进行过多转化和介入,反而直接采取景观化手法达到博人眼球、社会争议等公众效应(有意思的是,在同年宋拓参与的另一个展览“绝地通天”里,徐震®用罗马柱拼成的“METOO”字样大型雕塑却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反响,这或许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语言失效)。倘若观念艺术诞生之初的要义在于艺术家发现、指认和置换尚未被辨析、探讨现象的敏锐触角,那在2021年展出《校花》不仅不再具有这种前置性,甚至已经滞后于公共领域的观念更迭。近年来,从高校、大型企业到文娱界的各类性别暴力事件引发持续的社会关注与反思,媒体讨论逐渐形塑起一套新的描述与辨析社会内部性别结构、个体经验和权力关系的公共话语,公众对相关视觉与图像传播的批判性观察与认知也日趋敏锐。这些观念的积蓄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把校花事件中的公众反应放在一系列社会舆情事件的链条中理解,更提醒长期处于“例外状态”并享受一定“豁免权”的艺术行业反观其观念与实践和社会现实的距离。

与此同时,艺术评论界也存在着一种“力量修辞”。这种修辞把作品对观众的压倒性震撼“反证”成批判和激进,以此来掩饰景观化生产自身的观念贫瘠与无效。事实上,批判的本质从来都在于观念的异质性,而非力量的强弱。而将对既定社会结构的复制、确认与强化等同于挑战和前卫的逻辑也引出了另一类为作品附魅的因素,即,强调艺术家在工作过程中调度社会资源、与权力系统周旋的能力,并将之视为艺术家工作的核心内容。不过我们却甚少在此类评论中读到有关艺术家如何调度、如何周旋的具体描述(像是如何获取政府资源,或如何说服资本投入),亦很少去追究艺术家是否利用了原有社会生产结构的不平等来表现自己的“能力”。究其根本,这种强势却单调的叙事对艺术家身份的定义依然建立在前现代时期以降艺术家“天赋异禀”、“能力超群”的观念上,不论这种才能是逼真再现的技巧还是调度社会资源的手腕。校花事件恰恰指出了此类陈旧的身份定义已经失效,也警醒艺术界对之展开必要的观念制衡,以一种更为深入的实践自觉在艺术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寻求各方主体性的双向激发、重置与再度联结,以此为基础重新想象艺术生产与社会场域的多样关系。
校花事件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社交媒体和网络舆论在作品流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项事件中公认的事实是艺术家言论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自作品于2013年在“ON | 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展出直到此次事件爆发前,艺术家对其创作理念的解释大多采用玩世不恭的口吻。他一方面强调对排名的“决不妥协”及其真理性质,同时对近年来性别相关公共讨论的诸多概念加以调侃和戏谑——“物化”女性也是一种“尊重”,两性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的争夺等等。这种表演性和模糊性令言辞与艺术家实际意图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再能被证实或证伪,我们因而可以称言论是具有后真相属性的。这一属性在艺术家访谈和展厅文字成型之际便已确立,但它如何发挥效果却取决于作品实际的流通情况。本年六月的舆情中有三个关键因素:不同群体对言论的解读分歧,质疑者对言论和作品中“问题”的鲜明辨识,以及艺术家的全面隐身。如《冒犯的艺术》所言,艺术圈以往对此类言论常常采取“认真你就输了”的犬儒态度, 并因此令言论和作品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审视。公众的质疑则清晰聚焦了其中的“问题”,言论不再能被撇到一边,被聚焦的“问题”随即成为审视作品的必要环节。
公众质疑带来的二度检审激活了言论的“后真相”属性。事实上,“问题”一旦进入后真相状态,就成了一种无法被证实或证伪——也因此无法被彻底排除的可能性。作为一种阴谋论般的存在,它抗拒并消解一切对之的回避、否定和质疑(不论是对言论的不知情,还是到作品中用主观认知努力去撤销“问题”)。而当我们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犬儒主义者的长期默许和放弃辨析则无异于是与阴谋论共舞。再者,艺术家的隐身无论是否出于清晰的策略考量,但结果就是加剧了其在后真相空间中对信息源的垄断。此时,除非展览机制有能力改写艺术家与参观者之间的权力配比,以确保公众在作品中反思与行动的充分自主,否则留给后者展开符合其道德自觉的质疑、行动与思考的空间实际寥寥无几。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事件议论的走向视为艺术家的后真相舆论操作与当前中文网络生态的内在复杂性相互碰撞的结果。在社会公共讨论层面,艺术家的极化修辞切中网络舆论情绪先行的特质,公众反应也因而可以预期地呈现出网络霸凌的极端化倾向。在艺术话语流通层面,当观念艺术的解释话语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评论套路,艺术圈与公众在语言上的关系也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和互不通约的特征。业内人士看似理性的说辞既反衬出公众言论的粗粝与偏激,也为作品提供了合理化的温床。当下,各领域的知识生态正走向多向度的异质性联结和越发丰富的公共表达,艺术界也有必要重新激活僵化的评论话语,打破与公众的无效沟通。

校花事件的后续讨论最终陷入了非此即彼、相互割裂的两难境地——政治正确 vs 艺术自由、社会观念 vs 艺术表达。这种更像是时代思维定式的割裂状态是否真的无解?倘若前几年政治正确话语在艺术界的回响仍停留在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遭遇的观念质疑(最明显的自然是2017年古根海姆美术馆“1989年之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一展引发的争议),艺术行业此刻该如何理解、应对此次事件中来自最广泛本土民意的剧烈呼声?艺术表达的自由又该如何与这般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和观念共处、互动?我们不难注意到近年来“政治不正确”在国内艺术界的流行,有人甚至把刻意表演政治不正确视为“批判”、“诚恳”乃至“追求自由”的标志。但故意的政治不正确并无法带来对政治正确的有效批判,艺术自主性也不是必须以颠覆社会观念为代价来达成。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中逻辑的不自洽,更要有勇气超越这种实际毫无建设性的观念分化。
分析至此,一系列关键词浮现出来——后真相、阴谋论、情绪操纵、极化修辞与观念分化、对政治正确的逆反姿态。它们都直指当前公共生态内部的种种结构性疑难,也折射出社会心态和观念在持续的地缘政治张力和疫情焦虑下令人忧虑的变异和演化。这些现实疑难在校花事件作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得到清晰的表征,还为艺术家以后真相姿态介入其中,展开一系列侵蚀公众思考与行动自主性的舆论操作提供了绝佳情境。对此,我们不得不展开追问:在情绪化、观念分化、后真相的公共生态下,当代艺术是否有能力重新定义自身?而我们作为形塑公共生态的社会主体又该如何应对、如何捍卫我们共同的自主意识空间?当艺术界与社会公众在媒体与展览生态中走向越发开放而激荡的互动关系,当公众意识与话语在一次次碰撞中起伏开阖,艺术界也亟待建立新的主体性和话语体系,从种种二元对立的抗辩状态里挣脱出来,在创作者、公众与评论者之间寻找、开拓观念上的联结与共同行动的可能。
钱文逸,艺术史学者、译者,关心手工艺、认知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研究近代早期欧洲,但也关注现代时期欧美与东亚间的观念互动和翻译政治。
文/ 钱文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