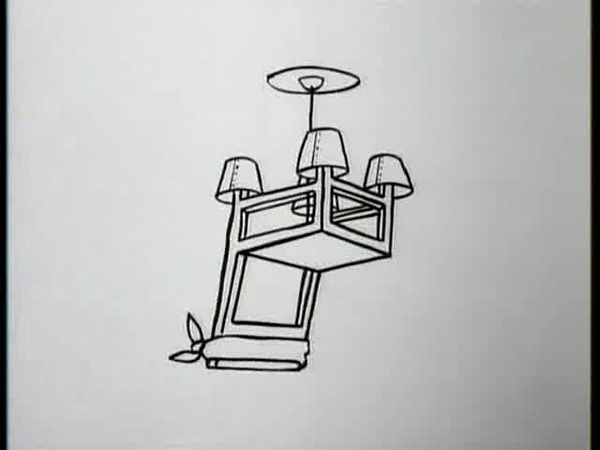马修·伯利塞维兹(Mathieu Borysevicz)谈MABSOCIETY以及BANK
离开“外滩三号”后,我从2012年起就有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做一些外面的策展项目,也出版一些东西,比如今年出了这本关于徐冰的书(《关于徐冰的地书之书》),同时也在做一些独立代理(independent dealing)的工作。我觉得与其用我自己的名字去做事情,不如把它扩大一点,找到一些合作的朋友,所以我们有了MABSOCIETY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策展办公室或者策展机构(curatorial studio)。一开始我们的办公室是朋友给我们免费用的,在一个写字楼的23层,但一直都不是很适合我们,比如吊顶、日光灯什么的;后来也赶上了房子到期,我就觉得我们该换个地方。然后突然这个地方(BANK,位于外滩的前银行工会大楼内)就出现了,我本来没想找一个做艺术空间或者画廊之类的地方,但一直都想找一个小的项目空间,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项目,可以摆出来一些作品,一个又能工作又能玩儿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爱上了她:位置好,空间比我想象得大多了,这里又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除了展览以外你还可以看这个建筑。我觉得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跟其他同规模的城市相比,包括北京,艺术活动不是特别多,两三千万的人口,艺术气氛还是比较低调,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老的国营单位的楼,这个楼现在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稳定,不知道我们能在这里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楼什么时候对外开放或者要装修。反正能留在这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