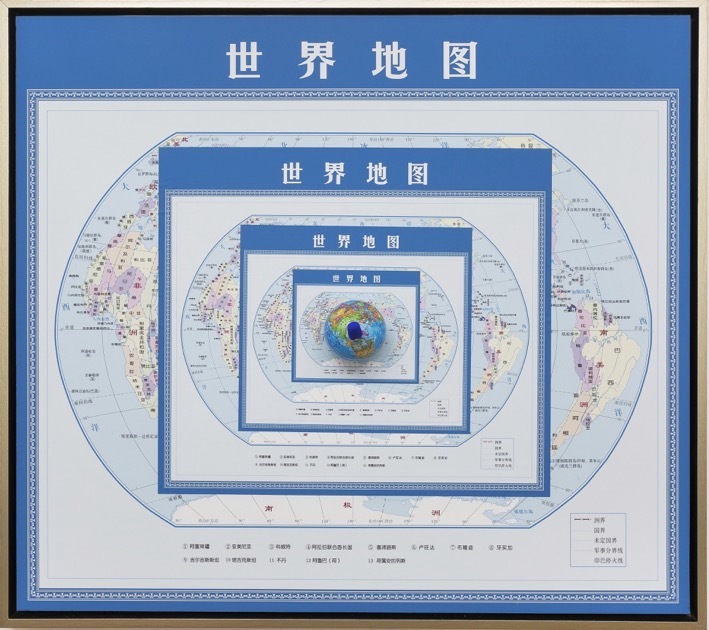苏文祥谈“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
在展览“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中,黄山和庐山两部分老照片及相关文献被分别占据了两个主展厅。这些照片大部分来自泰康的收藏,从中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般风光摄影的一些面貌;而照片及照片中的两座名山又与建国初期的革命、政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常与革命”的命题下可以窥见两种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牵连的风景。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
回溯历史、挖掘过去的材料这个主导思想,泰康空间在很多年前就明确下来了。从我个人来讲,2012年底的“华北农村1947-1948”展是一个萌芽,到了2015年“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时想法开始迸发,一种基于对图像的分析——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新中国早期革命史的背景下进行的考察工作。“日常与革命”和“白求恩”的明显不同在于此次作品是我们非常熟悉、能亲眼见到实物的照片,因而在整理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想法:当我们给它镶上镜框的时候,它其实退化为一个图像。我们为了还原照片作为一个物的属性,对其进行扫描和抠图。白边、破损、变黄和某个折角都得以保留,最终做成了一段照片影像,将影像(照片)再次影像化(视频)。有意思的是,这段关于黄山的影像与另一段网上下载的黄山旅游视频在内容、拍摄角度上惊人地一致。它们被展示在同一个展厅里,常常出现“同步”的画面。
展览中的黄山部分以吴印咸的作品为主要背景,还包括黄翔、吴寅伯、陈复礼和袁廉民等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