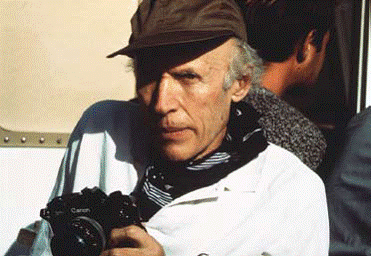詹姆斯·匡特(James Quandt)谈大岛渚(Nagisa Oshima)
“大岛渚是个混蛋。不管你做什么,别邀请他!” 1988年,当我在筹划一个日本大师电影回顾展时,不止一个同事曾这样劝我。幸运的是,我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大岛渚是最为通情达理的嘉宾,他慷慨,有趣,意料之外的安静, 和我分享了彼时对于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电影的热情,并就着威士忌用一段放松而有趣的问答环节回馈了多伦多观众——“请给我下一部电影的钱吧!” 在放映完《马克思,我的爱》(Max, Mon Amour,1986),他半是嘲讽,半是恳求地说。当他在安大略美术馆遇见突然来访的疯狂日本游客,他则巧妙地调转方向得以脱身。(相比较电影导演,他在日本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直率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兼时髦花花公子 。)在所有战后电影里,这位愤怒的反叛份子的作品是最具腐蚀性的——大岛渚曾说,“我要与一切权威和权力作斗争。” 他引发各种丑闻的电影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看似镇定自若,却很有吸引力地闪烁其词;当我问起1960年后他电影里不断出现的同性恋情结时(这比他最后一部电影、表现同性题材到极致的《御法度》(Gohatto, 1999)还要早很多年)大岛渚无辜地笑了笑: “这很有趣啊,难道不是吗?”
大岛渚出生于京都一个有名望的家族,他的父亲曾为武士贵族工作。利用父亲丰富的图书资源,大岛渚很早就阅读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著作,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电影创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