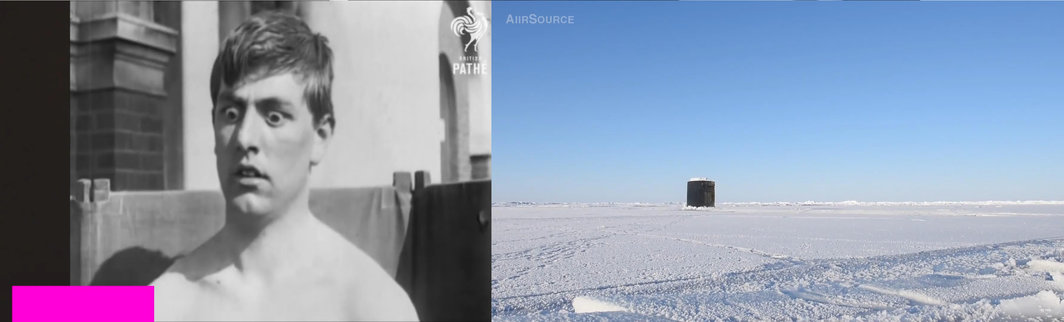
金锋:万恶之首
在观看这场布置于斜坡之上的展览过程中,观众需要不断在水平和倾斜两种角度之间切换视线。这种平衡感的不稳定多少干扰着对作品的阅读。但就某种程度而言,它也是金锋本次触及生态学的展览所必需的一个地形:展览从一个类似议院内部阶梯座椅的绿幕舞台开始(五位演员──丁博、疯子XX、刘亚囡、张楠、郑力敏──在此以表演回应展览提出的议题),引导观众沿着斜坡向上逡行至最高处的《珠峰门》(2016)。坡道顶端的这件双频道录像作品以山峰海浪这类国家地理频道式的影像为底,配上各国元首在峰会中谈论碳排放标准的视频。其中讨论的生态学问题几乎是对既有大众媒体报道的复制。金锋更多关注的还是该议题如何经过大众媒体转化,成为另一种定义全球现实政治的方式:自然界的崇高式影像,在元首谈判中不过是以碳排放的形式作为博弈的筹码。自上而下看,展览中部坡道上的作品被艺术家安排得像是弹珠机台上散开陈列的障碍物。《坡道戏剧》项目的演员刘亚囡的表演就在这里进行:怀孕的她在自己鼓胀的腹部(她还在衣服下塞了棉花,以突显孕妇的身型)和瑜伽健身球之间建立起某种比拟关系。表演期间,她带着体内与体外两个大球,缓慢地滚进沿途各个装置作品中,复又弹出。
就此而言,可以说某种生物拟仿的策略回应着金锋——以及本次展览策展人宋轶——所谈论的生态学。这种关于生物拟仿的问题,也在录像《更好的版本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