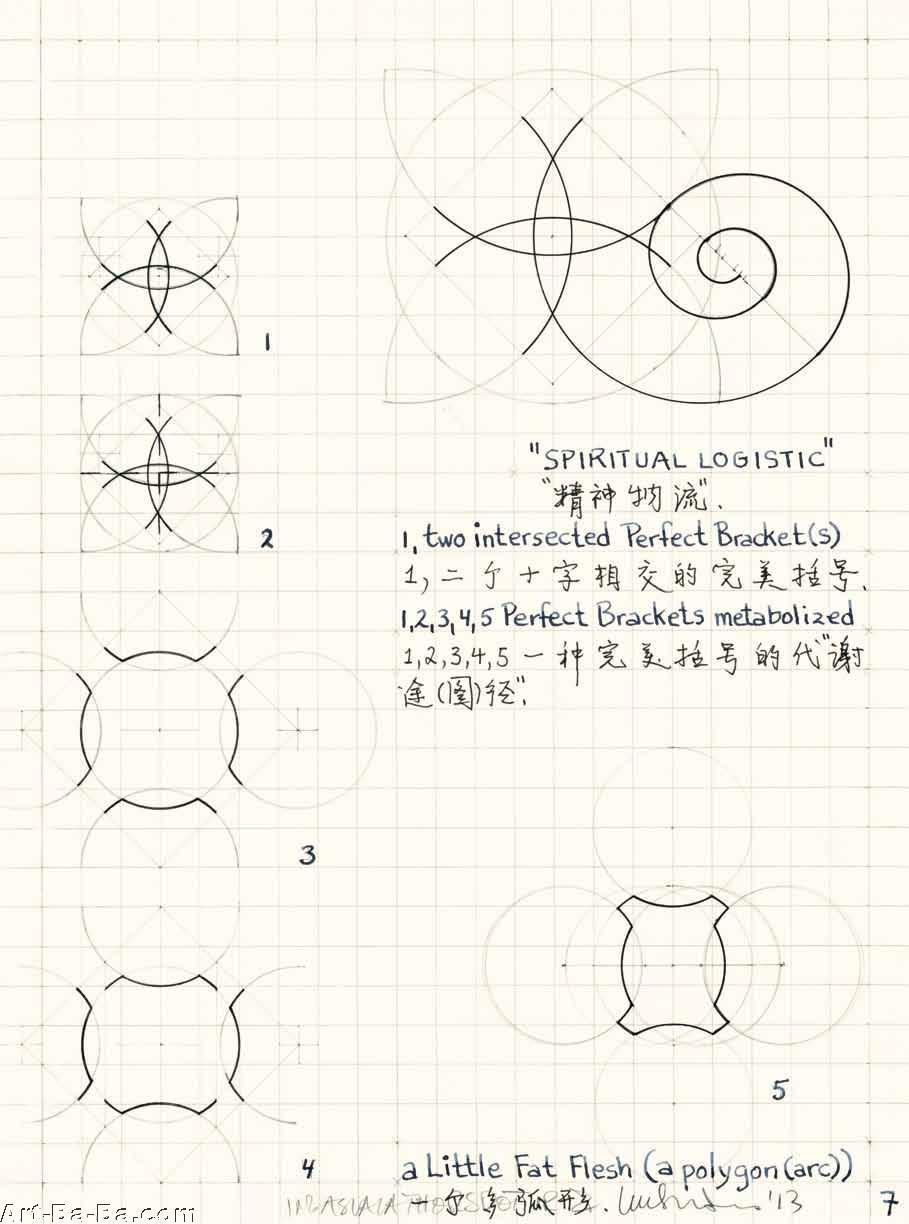他/她从海上来
对于深圳这座移民城市而言,展览主题中事关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的暗指无疑引人瞩目,相比OCT当代艺术中心以往晦涩、以学术为纲的展览亦清新许多。然而,缺乏细致的田野调查构成了它的短板,轻而易举的惯习仍然显著的束缚着它——比如,艺术世界中的精英主义,虽然其注重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构成的话语网络。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到艺术家对于互动的渴望:在郑波的《为伊唱》(2013)中,观众被怂恿着在展厅里喊叫,跟随录像一起唱歌,艺术家希望参与者暂时打开自我,以这样袒露的方式介入到他者的记忆中。然而问题在于,策展人和艺术家是否做到了同等程度的自我剖析?
从某种程度上,“他/她从海上来”的态度过度依赖于全球化的舶来经验。例如《第11号案例:塔林辛基》(2016),其与本次展览主题仅呈现微弱的关联,却在不大的展厅里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而更多有趣的、植根于本土记忆的作品却在此缺席了。李燎的《退到世界之窗》(2012)也许最真诚且最具田野气质,其反向回溯了一代移民的集体记忆,对观者的触动远远超过汇编式的作品。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即艺术家仅仅用触手可及的原料和行为,就能够创造出动人的作品。毕竟,这是一个处于珠三角、为了珠三角的展览,为什么需要塔林港和赫尔辛基来做注脚呢?是由于我们尚未产生足够诚挚的作品,还是由于我们对西方话语的过度依赖以及对于后殖民的念念不忘?
在一些呈现中,西方视角始终未加处理的横亘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