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FILM & VID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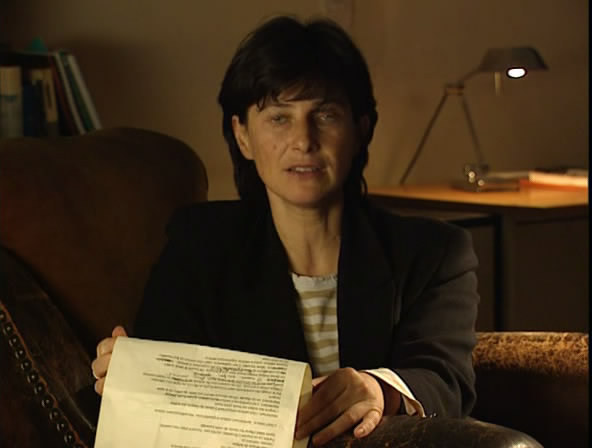
原文发表于《艺术论坛》2004年4月刊。
《在她的时间中(一)》请点击这里。
罗森:你曾说“为了拍摄电影,你还是得写作”,但也许这句话应该为“为了让我拍出电影…”
阿克曼:不,不。不是为我,是因为必须筹到钱来拍电影。这其实正适合我,这对我有好处。因为开始写作的那一刻——我喜欢它。 但是对于现在的纪录片来说,他们希望我的写作能够更加明晰,但我完全没办法使事物变得明确。所以我就来回来去兜圈子。我围绕着电影来写,围绕着那个空洞——或者说是,空缺。因为我就是想去拍纪录片,即使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将怎么做。他们总是要求说“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而我能说的只是我不知道。这源于对那里可以孕育出一部电影的认知缺席。
罗森:说到时间,我想今天的人们对于你的工作方式或许更为习惯。它并不遵从于主流电影的规范,但它体现出最为常态和最为人类本性的东西。
阿克曼:你知道,对于大部分去看电影的人来说,对影片的终极褒奖便是——“我们并未感觉到时间的流走。”而对我来说,观众在我的影片里目睹着时间的经过、并感觉到它。它们让你感受到这便是流向死亡的时间。我想,我的影片里确实有那么一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观众对此产生了抗拒。我取走了他们生命中的两小时时间。
罗森:但我们毕竟感受到了那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不是处于堵车的煎熬或在看电视。
阿克曼:对,我同意。但并不只是这样。正相反,我发现在那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只因为在那之中,我们处在凌驾于信息之上的某处。比如在《来自东方》里,我们看到排队的人群,而那个镜头持续了七八分钟之长。而现在,每当我母亲看到有关于俄罗斯的新闻,她便会说:“我无法不想起你的电影。我再也不能用以往的方式来看待关于俄罗斯的新闻了。”这是一点。而对于我母亲那一代人来说,他们透过电影看到了自身。比如我母亲便在《来自远方》中认出了她过去的衣着,她对影片中的面孔感到熟悉。那些画面本就在她的头脑中。对于在战后出生的我来说,当我拍摄那部影片时,我总是问自己为什么我拍了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但我并不知晓答案。但当电影完成后,我意识到那些特别的画面其实早就在我的脑海之中,(透过电影)我将它们唤醒。
我在此处所谈的是纪录片。在所有这些所谓的纪录片中,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刚刚只说到了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但它们也可能唤起了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记忆,也许是露营或战时的队列。在《南方》(Sud,1999)中,一棵树使人想到一个黑人可能在这里被吊死。如果你只展示两秒钟,这一层含义便会缺席——那只是一棵树而已。我想,是时间将之确立。
罗森:你的影片另一特征便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音乐性。我说的不仅仅是读信、或是那些对话,还有你自己的声音——装置作品《近乎虚构:来自东方》(1995)里的法语、英语和希伯来语;以及《另一边》里的西班牙语。它们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阿克曼:这些有关于母语,一个人要么拥有它,要么不。我是第一代比利时人。我母亲在她十岁时来到这里。她的法语里藏着那么一种波兰语的音乐性,她岁数越大,便越明显。她会省略le和la的冠词,比如她现在会像波兰语那样说“我去医生。”我从小也在希伯来语的歌曲和祈祷文中长大。所以我的写作中会有希伯来语的音韵反复出现。
罗森:我在阅读和重读你的小说《布鲁塞尔家庭》(Une Famille à Bruxelles,1998)时听出来了:里面的句法非常简洁。于是我突然意识到那就像是圣经希伯来语,带着那种重复——和,和,和!(and, and, and!)
阿克曼:于是上帝说…和…和…和。是那样的,没错。我小的时候是我母亲的法语和犹太语的混合体,因为我的祖父照顾我,他不说法语,他总带我去犹太教堂。
罗森:你也说意第绪语(Yiddish)吗?
阿克曼:我能听懂,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在九岁时被带离了迈蒙尼德学校,因为祖父在那段时间里去世。要不然的话,我想我肯定会精通希伯来语、意第绪语,以及所有那些。
而现在我的语言相当贫乏,我的词汇量有限。德勒兹在谈论卡夫卡的语言和“少数族文学”(minor literature)时对此解释得极为恰当——没有重大交通事故,没有特殊效果,所有事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密。
罗森:我想如果你戳透一点表面来看,每个人几乎都是“少数族”。
阿克曼:在法国不是。
罗森:是的,在法国,的确如此。如果你戳穿的话。
阿克曼:首先,那里有着庞大的非“边境居民”人群。还是有些人是属于那所谓的“土地”以及法语的。毕竟还是有“法国人”。
在美国——以纽约为例,其他地方也一样——那里有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即使你英语讲得很糟也没什么。但在法国或者比利时——比如,在我的第一份学校答卷上,老师批注了“(太过)口语化”。我上了“一流”的高中,但却从未感觉自己属于那里。我在很多方面都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我说话的方式上。在纽约,每个人都能听出来我来自法国或比利时,但我并不因此紧张。
罗森:为什么在二十一岁时选择了纽约?
阿克曼:就是有那种渴望。我不记得为什么了。我印象里那里发生着什么,虽然我不清楚是什么。到纽约时我只会很少的一些英文单词,但我学得相当快,我也从来不感到自己的英语说得差。在法国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存在“法国人”的。在纽约,虽然不属于那里,但我感到如释重负。而同时,我也不觉得我在那里拥有归属感。不过,那也是种乐趣。在法国,没有归属感可不是件令人轻松的事。
罗森:但如果你留在不得不谈吐“得体”的异国,那么选择在《迷惑》里改编普鲁斯特则多少有些平淡乏味了。你曾谈到“这本书是为我的电影而作的”——在《Les Inrockuptibles》(法国摇滚杂志)里——但是在所有那些词形变化、你本人的声音、时隐时现的口音中,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对“我在这里”、并且用法国经典文学创作的表态?
阿克曼:不,我不认为我是在证明自己已进入法国文学。对我来说,当我读到普鲁斯特的《女囚》中那些走廊、卧室等等之处时,我说道:那是我的!
罗森:我们已谈到时间和空间、你的电影剪辑、文本和语言、以及装置。但我们还未谈到画面。
阿克曼:大多数情况下我凭直觉创造画面。我起初不认为正面画面是偶像崇拜(idolatrous),因为它是与另一个人面对面。但后来我意识到了。观众在电影院观看电影时将坐在“我的位置”。这和有些人对于时间的评述类似:我们感觉到时间,从而感受到我们自己。在与画面面对面之中,我们感觉到自身。事情作用于别人时我们便总置身事外。普鲁斯特在谈到他亲吻祖母时说:“然而我亲吻的只是外部!”这使我深受震撼。我的电影便审视着这种外在性。这和时间一样,因为其他人对时间的感受也不尽相同。他自己的时间感起着作用,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起着作用,那是对你的直接凝视,无可否认。所以说这并不是窥私,如果你向上看、向下看、向两边看什么的,那你便是个窥私的观众。但在正面画面中,这不会发生。
罗森:装置《来自东方》的最后部分有一个孤零零的监视屏,以及你背诵十诫第二条的声音,这显然是禁止偶像崇拜的。这令我感到惊讶,因为这种禁令似乎非常困扰你。
阿克曼:是的,但这是之后的事,在我拍了很多电影以后。突然一下,我想到并对自己说,如果我制造这样的画面——前位画面(en face)——那便不是偶像崇拜了。无论怎样,这些都是事后的解释了。
罗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从来都不自己拍摄画面,而总是和摄影师一起工作——从最开始(的影片)一直到《另一边》中你使用了不同的媒介,包括你自己的小DV机。所以我好奇的是,作为一个总是独立行动的女性,你却并不自己操纵摄影机吗?
阿克曼:是的,但我总是和拍摄画面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我自己构图。我可能不会自己按下拍摄键,但我会自己打光。
罗森:最后,回到“少数族文学”上,你曾在二十五年前的一次访谈中谈论过这个话题。而现在我的问题是:对于你在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回顾展和所有这些——你已在巴黎波堡区(Beaubourg)得到认可,还在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 Gallery)有展览,实际上你已经不再算是“少数族”了。你对这种改变有何感受?
阿克曼:你是说我已经有点功成名就了?
罗森:不,我不认为你已功成名就,但你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这使你与世界的关系改变了。
阿克曼:是的,但我不那么感觉。坦率说,我根本不那么觉得。我清楚我必须继续工作,坚持下去。有天我经过波堡区时,看到那里挂着很大的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名字,于是我对自己说:“嗨,我的名字会在这里那样展示吗?”不过后来,我就想别的了。
米里亚姆·罗森(Miriam Rosen),作家,现生活在巴黎。
文/ 米里亚姆·罗森(Miriam Rosen),译 /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