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月份,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刚刚过了一百岁的生日,但大西洋这一岸,却几乎无人对此进行欢呼,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当然研讨会,新的出版物,以及有关宣言的零星文字还是有的,而今秋的Performa也将献给百年庆;不过,除了纽约MoMA教育和研究楼地下室的一系列橱窗以及蒙特利尔加拿大建筑中心和迈阿密海岸Wolfsonian-Florida国际大学组织的《速度极限》展外,北美博物馆前沿的沉默令人纳罕,尤其是想到未来主义对历史先锋的重要性,这种无动于衷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说起来,似乎又情有可原:因为未来主义本来就是要捣毁博物馆—一个他们视之为当代艺术毒瘤的机构。无论是知识上、意识形态上还是实际的原因,眼下的这种沉默(例如,对于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宣言毫无耐心,对于其通过战争和对女人的鄙视来净化社会而感到反感,很多最好的图片已经被借用出去)与另一畔的欧洲大陆的热热闹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一年的时间里,都在为之举行着百年庆祝活动。
在米兰,罗马,罗维雷托, 重要的百年展已经开幕,其他的还有在威尼斯,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大多数展览都出版了学术性的画册,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犀利,夹杂着不同的声音,人们如圣徒祭祀般纷纷来到了现场。那些活动,就如那场运动本身一样,都蔓延到了大街上:为了纪念未来主义对于机械化运输的热情,一辆“未来电车”在今春穿过了米兰的大街,而这场运动对厨房的渗透也造访了罗马的Taverna dei Futuristi,那里的菜单有未来主义诗人保罗•巴兹(Paolo Buzzi)编撰的意大利米饭risotto all’alchechingio。
周年展一般都是与某位艺术家的生日相同步的,但是在这场纪念展中,人们庆祝的是一场大众媒体的活动,也许它是首个由这样一位艺术界的代表所指导的活动:1909年2月20日巴黎《费加罗报》首页《未来主义的成立和宣言》发表。文章由亚历山大出生的法意诗人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撰写,他最早的书面语言是法语,宣言声称要在美学和日常生活领域中,发动一场彻底的现代主义变革。马里内蒂否定了过去,要求在所有最为当代的表现形式中,产生出蓬勃而富有力量的现代性。尤其是那些与我们经验上的现实的加速相关的形式:“一辆跑车,比胜利女神像要美丽多了,”他向那些毫不怀疑的读者们呐喊道。
发布于意大利的这场运动的另类内容,为美学理论和实际开创了一个崭新而全面颠覆的平台,其作为宣言的这种表现形式,源于宗教和政治的传单,也许是《共产主义宣言》最为著名的例证。一位年轻的诗人对主流媒体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未来主义发展起来,迅速从文学扩大到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戏剧、时尚和电影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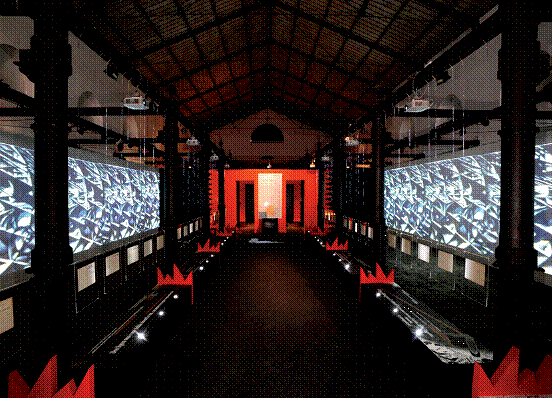
近期的展览围绕着马里内蒂在《费加罗报》的文章,而非早些时候出现在更为隐晦的意大利文、法文、墨西哥文和罗马尼亚出版物上的宣言,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因为在与后来的艺术史的关系上,它突出了未来主义以及它的敏锐度的独特性:其大胆的智慧性和理解力成功地在艺术界的中心地(巴黎)和边缘地(意大利)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解,开创性地将艺术作品作为宣传手段而重新定义。
两场百年纪念展的一场,直接是与未来主义依赖于宣言这种表现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MACRO Future的展览,第二个展览地点是在罗马的当代艺术中心。由阿希尔•波尼托•奥利维亚(Achille Bonito Oliva)策展,以音乐会的形式由基诺•迪•麦吉欧(Gino Di Maggio), 文森佐•卡帕尔波(Vincenzo Capalbo), 和知名的作曲家、表演者、未来主义的音乐家丹尼尔•伦巴迪(Daniele Lombardi)打造,通过一场独立的具有价值的文献和文章收藏而完整起来。(Fondazione Mudima, 2009)
前厅的两边,是很多小扩音器,将观众从罗马的阳光下引入了一件漆黑的、八十英尺长的画廊里。在这个像教堂中殿的空间的末端,悬挂着《费加罗报》一张原始的首页,挂在两个架子之间,被打上强光,几乎相当于文物被保护起来。就如听上去不那么合适一样,这一高度夸张的展示,在对未来主义的原始前提和我们自身的历史时刻上,有着一定程度的讽刺性,如今我们似乎每日都面临着首个真正称得上大众媒介的消失(或深刻变化)。
在展厅的两边是一系列数码录像投影,一些移动的画面出现在此,还有声音记录,纪实摄影,绘画和即时性作品,来自宣言的妙语,由卡帕尔波和马里雷纳•波特兹(Marilena Bertozzi)导演,伦巴迪和未来主义作曲家艾尔多•吉欧迪尼(Aldo Giuntini)和阿尔弗莱多•卡塞拉(Alfredo Casella)配乐,投影努力将被动的观众变成一名“参观的演员”,将他置于宣言的中心位置,就如未来主义画家贾柯莫•巴拉(Giacomo Balla), 乌姆伯托•波西尼(Umberto Boccioni), 卡罗•卡拉(Carlo Carra), 路易吉•卢瑟罗(Luigi Russolo), 吉诺•塞维里尼(Gino Severini)努力将观众置于画的中心一样。我并不觉得投影录像获得了这种客观性,但是它作为一种展现形式,确实激活了宣言本身这种形式,将它推向了一个具有共感性的统觉上。

投影引导并保持了观众对于展览上百个宣言的兴趣——它们都源于马里内蒂已故女儿鲁斯的收藏—-大多数在隔壁的展厅陈列,除了首页外,大部分都难以得到。这些文字由不同的未来主义成员们撰写,很显然都经过了马里内蒂的批准,最开始作为独立小册子,出现在很多的杂志,展览画册,书本上,强调了未来主义对所有可获得的书面媒体的灵活介入。第四展厅放映了很多关于这场运动的电影,最有趣的是卡帕尔伯和艾佐•戈多里(Ezio Godoli)的《未来主义大都会:在未来主义大都的视觉之旅》(1999/2006), 这是一部关于未来主义城市的数字动画片,在上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建筑学家安东尼奥桑特艾利亚(Antonio Sant’Elia)和弗吉里奥•马奇(Virgilio Marchi)曾为此提议过,他们优秀的画作将现代的公寓建筑转为车辆流通的集散地。
另一场突出未来主义纸媒特征的百年展是F. T. Marinetti – Futurismo, 由路易吉•桑索(Luigi Sansone)在米兰的Fondazione Stelline策划。虽然展览并不那么夸张,但它的题目成为未来主义充满挑衅的一部分,与一个世纪前关于运动所有权的争论相呼应,Marinettismo这一称呼将它的创办人置于了附属位置,抹掉了他的完全性控制。
我们会不会试图将展览的题目读解为具地方保护色彩的、主动进行的删减,甚至是故意为之的玩笑?很难回答。抛开别的不说,展览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对马里内蒂与视觉艺术持续性的关系之间的探索性,当然他也将不同的象征主义-新印象派画家引入到了运动中。在展览中,出现了诗人在不同媒介上的肖像,由国内外的人们所创作,其中包括所谓的俄罗斯未来主义鼻祖尼科莱•库宾(Nikolai Kulbin)所做的素描画,这位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艺术家邀请了马里内蒂在1914年来到这座城市;那不勒斯未来主义作家-艺术家弗朗西斯科•坎基洛(Francesco Cangiullo)所创作的大量少见的画作;马里内蒂的朋友,鲜为人知的波西米亚的罗吉纳•扎特科娃(Rougena Zatkova)所做的多媒介浮雕。
展览揭开了一个大秘密,人们发现,马里内蒂本人也是一个视觉艺术家。除了1921年的《Sudan-Parigi》外(一张先锋的多媒介拼贴画),展览还包括了不少纸上作品—一些随意涂抹的画—很多之前都没有展览过。描绘卡拉的人像画很棒,马里内蒂的笔几乎没有离开过纸,随意的线条将漫画艺术与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精妙结合起来。最突出的是诗人三十张左右的图文游戏拼贴,都是在1913年到1916年完成的,以未来主义早期最著名的文学创造parole in liberta为参考,为其命名为tavole parolibere,即“自由的文字”。受到无线电报、收音机、速记法等新技术的影响,这是一种破坏句法的文字构成模式;取消了副词,形容词,连词,标点;运用了不定式动词,拟声词,数学符号,音乐注解,动态字体。而马里内蒂努力将视觉的暗示向前推得更深:1919年他写道:自由中的文字,变成了自由图画中的文字和壁画诗歌。也就是说,诗变成了可观看的真实绘画,而非主张声明什么的文字构成。在Stelline, 有一幅之前未曾展出的长卷《Adrianopolis的爆炸:自由的未来主义文字》(1913), 作品是马里内蒂在Balkans为法国报纸担任占地记者而创作的;在英国诗人哈罗德•蒙罗(Harold Monro)在加州大学的档案中被发现, 可以说,这是诗人最重要的自由文字诗歌Zang Tumb Tumb (1914)的视觉副本。

沿着这条路,经过几条街区,就是Palazzo Reale, 这里展出了250多件作品,由吉奥瓦尼•利斯塔(Giovanni Lista)和埃达•玛索罗(Ada Masoero) 策划。展览的重点是这场运动的风格化发展,通过塑形活力从新印象画派的源头(也是它最为知名的一段时期)到20年代的“机械艺术”和30年代的“动感绘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沿着传统的艺术史链条发展的百年展,历史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风格。展览无所不包的特点,囊括了那些不太为人知的作品,如安里科•普兰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的全集(未来主义的第二代),但是,这种特点也使得展览变得松散而不集中。当然,松散也不是坏事,因为可以引入崭新的叙述方式,不过,这场展览并未做到这一点。
它以两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进行了终结:对于战后时期未来主义遗产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一间小放映厅里,观众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不错而又很难看到的未来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电影资料,有蒂娜•科德罗(Tina Cordero),吉多•马蒂纳(Guido Martina), 皮坡•奥里阿尼(Pippo Oriani)的Velocità(1930), 还有很多纪念意大利现代化的纪录片。部分是由于受到未来主义诗意性以及苏联电影创作的影响,这些影片都是由Istituto Luce制作,在三十年代是纳粹的宣传机构。那么,提起这番瓜葛,《未来主义1909-2009》是唯一从时间上讲述未来主义发展的作品,而在展厅里,任何关于这场运动在二三十年代与法西斯主义有关的讨论都几乎缺席。关于这场沉默,可以说,Palazzo Reale不是唯一。也许,这一话题和百年展的庆典调调并不相符。或者说,关于这场运动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历史性缺失、过于简单化与如今意大利右翼突然对未来主义报之以热情的接受,将其作为文化右派的美学表达有所关系?
“未来主义回到了米兰,”墙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宣布道,“这里是它的发祥地,在早期和那些有意思的日子里,这里是运动的地点。”这没错,但是,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展览《巴黎的未来主义-先锋大爆炸》却给了它一击。展览由迪迪耶•欧登杰(Didier Ottinger)和埃斯特•科恩(Ester Coen)以及马修•吉尔(Matthew Gale)策划,开启了2008年10月的庆典活动,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蓬皮杜展览的野心是将未来主义的起源在前前后后的起伏中定位,这场运动发生在巴黎,有意大利的画家,还有他们的同行们,不仅包括毕加索,布拉克,沙龙立体主义者们,还包括俄罗斯立体-未来主义者们,英国的漩涡派画家,它将1912年2月未来主义在巴黎Bernheim-Jeune画廊开拓性的展览重建,将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作品汇集在了一起。同时,它也努力将一场超越民族界限的运动发展进行定位,突出了巴黎作为各国艺术家云集地和这场运动发祥地的重要地位,而法语作为共同的语言,使得这种交流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展览对于巴黎未来主义的否定与同化,意味着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是一场国际性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性的运动。另一方面,它对法国在未来主义上的链条重新进行了归拢。
当展览来到了罗马的Scuderie del Quirinale时,它的委托人变成了科恩, 她将未来主义带回了家。对展览重新进行了修正,尽管保留了Bernheim-Jeune展览的大部分画作,广泛的主题性分组代替了历史性的重构。展览的前半部分,全都是意大利的油画和雕塑。只有先确定意大利的重要地位后,关于未来主义在国际上的传播这样的议题才可以被提及。在展览的第二半部分,科恩减少了沙龙立体主义的画作,法国未来主义者菲利克斯•戴尔•马勒(Felix Del Marle)只有一幅画被包含进去,而蓬皮杜展览中,他的画占据了半个展厅。在Scuderie,从美学上讲,最令人震撼的要属塞维里尼(Severini)和毕加索帖纸画了,以及阿尔登格索菲奇(Ardengo Soffici)和柳波夫•波波娃(Liubov Popova)的小油画。对面,是巴拉(Balla)的三幅抽象作品,标志着未来主义向前的发展;在最后的这些作品中,未来主义最终摆脱了死气沉沉、阻碍其发展的图形表现手法。
有趣的是,泛欧洲的现代主义和先锋运动全景图,成为了科恩在罗维雷托的MART独立策划的展览《未来主义宣言100×100:100周年/100次宣言》的中心主题。在所有的百年展中,MART展可以说是最大胆无畏的展览,它突出了一战前夕先锋创作的国际精神,将表现主义者、立体主义者、抽象画家都汇集到了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的柏林周刊Der Sturm(成立于1910年),还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者,立体未来主义者,光线主义者。与传统画册不同的是,展览的出版物是一本书,记录了米兰之外的未来主义的传播,每一部分都围绕着一个具体的城市展开,或者是两个城市一起:巴黎,柏林,佛罗伦萨-罗马,莫斯科,纽约。从档案性的资料里进行挑选,这本书成为了一本重要的学术性作品,体现了近二十年来的调查研究。
MART展览通过对具体客体的深思熟虑的并置,建立起一个共鸣的网络,而没有按照艺术史常规的单向路线进行,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和其他人作品,在此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通过将意大利艺术家和他们海外的先锋派兄弟们聚合起来,展览重新解读了未来主义:它强调了一直潜在于意大利运动中的抽象性元素,这一元素在早些年里并不明显。波丘尼(Boccioni)的大型油画《人体的活力》(1913),塞维里尼的《光下的舞者的形状》(1912),都值得一提。以萌芽状态的抽象性来思考未来主义,而不是强调图解的现代性,使得我们研究的课题变得疏离起来,从而给予它新的厚度和广度。在运动本身精神的推动下,MART对于未来主义的观点期待着下一场伟大的盛宴的开始—-即抽象主义的百年庆——是的,它很快就会到来。
作者玛瑞亚•高 (Maria Gough)为哈佛大学现代艺术Joseph Pulitzer Jr教授。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