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MIT Press出版了《于未来前夕》(On the Eve of the Future),那是学者安内特·米歇尔森(Annette Michelson)在过去三十年写的一系列关于电影的文章。文集的编辑瑞秋·切尔纳(Rachel Churner)在本文中采访了作者安内特·米歇尔森,两人就这本书的发展开始聊,从米歇尔森早期与巴黎五六十年代先锋电影的相遇,到之后她先驱性地将电影推为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对象,先是在《艺术论坛》,然后在《十月》——她是后者的创始编辑。
RACHEL CHURNER:《于未来前夕》是一部写作跨越三十年的电影论文集,从七十年代开始。书里的一些文章——你最早的一些关于电影的——是先发表在《艺术论坛》上的,或许我们可以从你怎么会给杂志撰稿开始聊?
ANNETTE MICHELSON:我刚从巴黎回来,我在那里居住了约十六年,当时,我给《艺术杂志(Arts Magazine)》和《艺术国际(Art International)》写东西,并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欧洲版撰写艺术评论。后来,我来到洛杉矶,一些读过我文章的艺术界朋友建议我应该拜访一下菲利普·莱德(Philip Leider),他是一本新的评论杂志《艺术论坛》的编辑。我便去拜访了他,他让我给他写。也差不多是那时候,我记得是在克莱蒙·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建议下,杂志搬到了纽约,他们说那里才是动向所在。但是我也在洛杉矶发现了许多大动向。
RC:你从1966年开始为杂志撰稿?
AM:是的,我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包括阿格内丝·马丁(Agnes Martin)和其他一些人的展评。当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的那些极重要的电影批评文章1967年以英语发表时,对我来说,这种特定的视觉表达形式同样应该在《艺术论坛》上有所地位。因此,我写了一篇关于他著作的文章(《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收于1968年春季刊《艺术论坛》)。据我所知,这是杂志上首次出现关于电影批评和史论的文章。我后来又写了更多。
RC:在1971年9月,你客座编辑了一期杂志,那期全部都是献给电影的。
AM:当时我甚至自己设计了那一期的排版,排版总是很好玩的。那几年我过得很好,我还邀请了其他我尊重的写作者,比如非凡的曼尼·法伯(Manny Farber),我认为他是那个为电影批评的原创性和专注性设下了标准的人,我从青少年起就开始读他。我也将我当时的一些极其聪慧的研究生带到了杂志的页面上。当我决定需要对日益剧烈的表演气候投入更多关注时,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开启了我们之间关于这个现场的对话。在60年代谢幕前不久,我遇到了罗瑟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我发现她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作者,我们立即成为了朋友。虽然将《艺术论坛》开辟为电影评论和理论的平台花了一点时间,但是我还是对菲利普怀有感激,他对于这个建议保持着开放态度,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编辑。后来,当约翰·科普兰斯(John Coplans)当编辑的时候,罗瑟琳和我离开了杂志,我们共同创办了《十月》,在那上面你可以找到我过去几十年间写作的种子。
RC:可以聊聊你怎么构思这本书的么?可以看出,你的标题表明,书是关于电影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女性身体。
AM:是的。标题《于未来前夕》有着双重指涉:一方面,我直接引用了作家奥古斯特·维利埃·德利勒-亚当(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的主要作品之一《未来前夕》(1886),那是一部令人着迷的科幻小说,关于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女人,成为机械生物。换句话说,《未来前夕》通过一个机器女人的形象折射了电影。
另一个指涉更加历史性。书里面,我写了一代独立电影导演跨越二十年的作品,大概是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他们都用16毫米摄像机拍摄,他们的影片可以说是创作于未来前夕,这个未来就是录像。
关于电影与身体的问题,我认为这本书的确涉及到,但这也和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关,那就是情色,当时的很多电影中都包含情色,诸如斯坦·布拉凯奇(Stan Brakhage)的主要作品《狗星人》(1961-64),再如霍沃尔的《切尔西女孩》(1966)。我从布拉凯奇的作品中看出,从他早期一直到他最成熟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对身体的赞颂。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作品试图实现罗伯特·惠特曼(Robert Whitman)作品中关于身体和感官的部分。《切尔西女孩》则相反,这部片子是带着愤怒和厌恶拍摄的,一点都不是庆贺的。顺带说一句,我曾经有一次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那是一件起诉波士顿某影院放映《切尔西女孩》的案子。
RC:电影院是不是被控以色情罪?
AM:是的,他们输了。当时是有个听证会,利奥·卡斯特里(Leo Castelli)派我去为电影辩护。当时庭上非常好玩。影院经历败诉了,但是法官对于我在他的声明中的辩护倒是表示了赞赏。
RC:正是因为这些电影中对身体的处理,使得它们在那个年代充满争议。然而在你的写作中,你也将身体视作为一种接纳的场所。在书中,你多次描写无论是《切尔西女孩》还是杜尚的《贫血电影》(1926)的观看体验,都是通过身体来记录的。我想知道你写的这种感官性的观看方式是不是部分来自你早期的观看体验?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电影时的情形?
AM:记得,而且非常生动。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早期观影体验和之后我对电影的看法之间的联系。我与电影的第一次相遇实际上非常令我不安。大约9岁的时候,我被带去看了神奇的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1931),那次把我吓坏了!里面的幽默我完全没有领会。多年后当我在巴黎再次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意识到当时我害怕的不是电影本身——虽然电影本身对当时的我来说也非常新奇,图像的大尺寸、黑白之间的高反差,以及对一些剪辑导致的不连贯都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真正把我吓到的是卓别林角色的一个情节,他扮演的流浪汉被一个富翁带回家,他们都喝醉了。后来两人开始泼洒酒精,泼得到处都是,包括互相身上,最后演变成为了一场跨越整个客厅的争斗,酒精在房间上空飞溅。这整个情节对我来说太过残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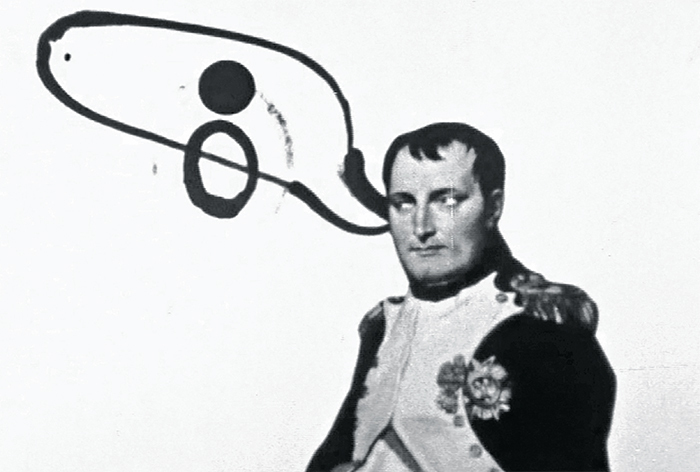
RC:你50年代初到了巴黎后经常看电影吗?你在巴黎住了好多年,期间经历了新浪潮的高峰,这对于你对电影制作的理解应该有极大的影响吧?
AM:那是肯定的。巴黎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值得看的作品的地方,当然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值得看的。我一直去看电影,居住在位于电影制作中心的城市实在是太棒了。你知道在法语里面有个说法吗?Paris bouffe tout——巴黎吞没一切。她绝对也吞没了电影工业,我们当时有种感觉是自己被电影包围了。那不是一种外国文化,在千里之外被制造出,电影正是我们位于其中的文化的一部分。
RC:你当时看了哪些早期导演的作品?当时有美国导演住在巴黎吗?
AM:有一些。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eer)是其中之一,也是我认为最有趣的一个。他是一位画家,因此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视觉感受。他也是伴随着一种对机械的感觉长大的,因为他的父亲是底特律一名重要的汽车设计师和工程师。布里尔极具智慧之眼,和他一起观看事物是很有趣的体验。和他交谈也非常有趣。他有极佳的艺术史背景,这是很多人没有的。我认为他是当时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中最有创造力和天赋的一个。他将形式之感和复杂性带入了动画电影,这一点我在别处没有见过。
肯尼思·安格(Kenneth Anger)当时也在那里,我第一次观看他的影片是在别人家里的墙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早期的作品,诸如《烟火》(1947),它们所蕴含的能量之大,以及其中囊括的电影文化之丰沛,他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凡。他的作品也富有勇气,因为其中包含了对同性色情的公开讨论,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他有一股想要将所有他见到的东西都纳入作品中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天真又是深思熟虑的。这种方式里面可能包含了从科克托(Jean Cocteau)那偷来的东西——的确是偷——但是同时使得安格能够挖掘出驱动他创作的电影形式装置。我在巴黎还看了其他人的作品,而布里尔和安格是最出色的两位艺术家——两种相反然而互补的气质。
RC:你那段时期的文章捕捉到了一个持久而关键的时刻,不仅在先锋电影里,还在表演里。这是由于你在纽约待过的缘故吗?
AM:是的。每五年我都会回到纽约待一段时间。当我1965年那次回去时,我发现那里正发生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事。当时在巴黎开画廊的依莉安娜·索纳本(Ileana Sonnabend)跟我介绍了贾德森纪念教堂,后来我一到纽约就过去了。我对于我所看到的感到非常惊喜,然后我就成为了贾德森的一员!我立即认识了鲍勃·莫里斯(Bob Morris)和依冯·瑞纳(Yvonne Rainer)——这俩人当时还是一对——后来我为莫里斯1969到1970年的回顾展写了画册文章《罗伯特·莫里斯,僭越的美学》,这是我回美国后发表的最初几篇文章之一。莫里斯后来没有和瑞纳一起表演了,我很想念曾经他们的合作,但是后来我愈发对瑞纳的作品感到着迷。我写了一篇长论文,1974年分两部分发表在《艺术论坛》上(1月刊的《舞者和舞蹈》和2月刊的《表演者的生活》),这两篇文章我都没有包括在《未来前夕》。这可能是个错误,在整理书稿的时候我可能觉得关于她的写作太多了,她自己也发表了不少,但后来我意识到之前的印象可能是来自过时的讯息。
RC:你见证了电影制作的巨大范围,以及技术为移动影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没有其他话题你考虑过收录但没有的?比如说,你考虑过收录你写《2001:太空漫游》(1968)的文章《太空中的身体:电影作为肉身知识》(《艺术论坛》1969年2月刊)吗?
AM:那篇是我文章中最为广泛阅读和发表的一篇,但当我筹备这本书时,我重读了这篇,很庆幸自己没有收录。(笑)这篇在写作的时候是满腹热情的,我至今认为我有理由如此,并且我依旧觉得我对于这部电影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是文章中的语调以及文学和哲学引用的数量多得有些幼稚。米高梅的曼哈顿负责人当时读了这篇文章,并从售票厅那得知,有一个疯狂的生物全年不断来看此片,并买了23张单人票,全都要求同一个座位(第三排,影院中间)。他给我带来了来自库布里克的邀请,诚邀我旁观他下一部电影《拿破仑》在南斯拉夫的拍摄。然而,《2001》第一年的票房太低了,后面的项目就被取消了,库布里克也因此进入了前卫电影导演的行列。我曾经想要写一篇文章叫《两个斯坦利的作品》,在里面我会将库布里克和布拉凯奇的创作相提并论。你不可能找到比这两位斯坦利之间更加迥异的创作方式了,虽然两位都坚持独立,但是他们独立于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
RC:有没有别的议题或对象是你希望自己写过的?你提到你非常欣赏布里尔的电影,但是你从来没有写过他,是吧?
AM:我生涯中的巨大遗憾就是没有写过布里尔。我尊重他的工作,他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两件事情是我不愿说出的,布里尔是其中之一。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解释。
也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从来都没有写过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的戏剧,我认为其在戏剧史中,以及在我与戏剧之间关系的私人历史中是举足轻重的。布里尔和福尔曼,我现在想到时觉得,这两人都做出了深度独创的作品,并改变了电影和戏剧的本质。最近我收到一本写很有意思的写布鲁斯·考纳(Bruce Conner)的书《寻找布鲁斯·考纳》(2012),作者是凯文·哈驰(Kevin Hatch),这本书让我联想到自己与考纳作品神奇的第一次相遇,没有写他也是一个遗憾。
RC:可以想象看到这本书出炉既令人高兴又充满挑战,因为这等同于目睹你毕生的工作付诸纸上。
AM:是的。(笑)我觉得每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在很早前就应该出版了。
文/ 安奈特·米克尔森 | Annette Michelson,瑞秋·彻纳 | Rachel Churner
译/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