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551年夏,地中海东部发生巨型地震。那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末期。贝鲁特当时以其法律学校闻名于世。这座城市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曾几度被试图抢占她那重要港口的凶残部队摧毁,又几度经历重建。公元551年的这次大地震引发了大火、山体滑坡和要命的海啸,使得海水倒灌,淹没了海岸线。贝鲁特被夷为平地。超过三万五千人死亡。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城市一直是一座废墟。
今天的黎巴嫩境内有三条主要的断层线。它们几乎是平行的,从南延伸至北:一条穿过国土的中线,一条沿着海岸线展开,还有一条位于东部的山区。自551年以来,这里又曾发生过数次地震,1759年的那次夺去了四万人的生命,1956年,无数的道路和居所被摧毁。据科学预测,贝鲁特很快将遭遇另一次大地震。
2020年8月4日,巨大的爆炸撼动了整个城市,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相信这是预期中再次将贝鲁特夷为平地的大地震终于到来了。大地颤抖,楼群晃动,玻璃碎成一片。这似乎是这充斥着非自然的碰撞和裂痕的丑陋、混乱的一年最后、最致命的一击。如果从政治而非地理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已经在很多个层面摇摇欲坠:经济崩溃、民众抗议以及瘟疫蔓延。
所有关于这个国家之坚韧、复杂和生命之喜悦的幻象都已褪去。这个地方由一群宗教领袖统治着,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从前的军阀,他们控制下的庇护主义网络如同利齿一般嵌入公共机关以及军队。这些人——从高级官员到微末小官僚——全都是些腐败的窃贼。自黎巴嫩内战结束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中饱私囊,徇私舞弊,收取贿赂,破坏公共工作和设施,用外表光鲜的假相掩盖长年发展停滞的现实,并且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愈发贫困和绝望。

“Al-thawra”的氛围——即革命,或者说抗议活动,从去年秋天开始爆发——几乎是全然暗淡的,有时不乏乌托邦色彩,但更多时候十分虚无。一些人敲响了锅子和盆子,但也有些人戴上了全副防毒面具、头盔和建筑手套,他们破坏建筑的外立面,并且向士兵投掷各式物件。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他们被称作“al-sulta”,意思是“掌握权力或权威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抗议者们咒骂他们,尤其是针对其中一位臭名昭著的内阁大臣。而所谓的维安势力则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小号铅弹来对付抗议者。政府利用Coivd-19的种种限制来粉碎人们的团结精神、批判和异议。与此同时,经济也出现了阵痛,政府无力偿还债务,银行启动了资本管制(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货币贬值近80%,工资变得一钱不值,而且人们的存款也相当于烟消云散了。
到今年夏天为止,根据《金融时报》记者大卫·加德纳(David Gardner)的报道,黎巴嫩“的经济萎缩之快几乎无法计量……国家一般不会破产,但黎巴嫩会。”8月4日的爆炸最开始被报道成一次暗杀行动或是以色列的空袭,结果却是一场由于政府渎职造成的工业事故,用加德纳的干脆利落的话来说:“一个对公共福利、安全和公共货品完全不关心的无能政府的缩影。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走向失败的国家。”
我们这些开始以为是场地震的人是幸运的。我们还有时间思考,而不是被抛到空中或者冲击到墙上或栏杆上或者脸上被突然飞来的无数玻璃碎屑击中。我们没有随着车子一起爆炸或是被埋葬在自己家中。我们也无需缝上400针或是装上两个义肢再或者要花上一辈子时间做复健。我们的后背没有没被那么多的玻璃划伤,我们的内脏也没有裂开。我们还有能力做些微的理性思考,将可怕的身体性的感受与不幸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
但当我们意识到这场灾难的真正起因是什么,地震感觉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了。地震至少还是可以测量和分析的,还有数据可言。事实上我们却是经历了举世最荒唐最愚蠢的笑话。一个无能的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将2750吨易爆炸的硝酸铵在港口——亦是城市的历史中心——疏于管理的仓库内放置了六年时间,直到它爆炸,摧毁了居民区、医院,摧毁了生命。有近两百人在这次的事故中丧生,六千余人受伤,三十万人无家可归。很有可能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谁该负这个责任。

“艺术家们怎么想呢?”写作者丽娜·穆尼耶(Lina Mounzer)问道,在回答她自己提的这个问题前就能看到她口罩后眼睛里的笑意:“谁他妈的在乎艺术家想什么呢!”这是爆炸发生后两个半星期,我们想办法绕过层层关卡,来到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或者是因为疫情的隔离措施,或者是因为爆炸后的紧急法令(谁说的清呢?),这里一反常态地关闭了,只对极少数的核心职员开放。我们坐在凳子上,俯视着深蓝色的大海,穆尼耶跟我讲起革命刚开始时的故事,那是在2019年10月,一群艺术家和写作者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化工作”。其中一些早期的会议是在下城一座孤零零的萨洛娃·劳乌达·仇卡(Saloua Raouda Choucair)的公共雕塑旁的花园里举办的。最开始的时候会议上洋溢着一种兴奋感,人们谈论着艺术家和写作者在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可以扮演的角色,随后辩论变得激烈并且严厉,艺术家是否真的可以在一场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阶级斗争中有所贡献?
穆尼耶回忆说,在十月的会议上,“我们只是人群中的人。首要的任务是走到街头,站在一起并且歌唱。”她停顿了一下。“那很美,也很动感情。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已经失败了”,她说,指的是改变统治这个国家的系统的斗争。但是抗议打破了那些评论这个系统的种种禁忌;一种广为传播的厌恶感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黎巴嫩人一贯秉持的过分实事求是和布尔乔亚式的谨慎,我们要求真正的改变。“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这些讨论过后,如“Amileen wa Amilaat”(阿拉伯语里“工人”一词的阴阳性形式)和“Mihaniyeen wa Mihaniyaat”(阿拉伯语里“技术人员”的阴阳性形式)等组织使得这股势头持续了下去,并且借鉴了集体行动长久未被提及的历史——通过工会、贸易组织,甚至社区和保护租户利益的社群组织——被黎巴嫩战后统治精英阶层系统性地压制,伤害了公共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视觉和表演艺术(极度边缘化)以及公立学校(其资金和资源都严重不足)。
穆尼耶跟我谈起优先级的问题,因为爆炸造成了新的急迫问题,而艺术家们一直都在与这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斗争。爆炸对艺术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国家博物馆和苏索克美术馆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多家画廊彻底损毁。艺术家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室、材料和档案。设计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展示间和工作室变成废墟。艺术组织原本就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苦苦挣扎,这次更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这个让人心痛的单子里还没囊括那些让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人日常的巨大努力,他们或者已经遇难,或者深受重伤,再或者既无钱修复自己的家,也没有其他国家可去。

爆炸过后紧接着而来的是捐款的热潮——很多团结基金和紧急拨款以及GoFundMe活动——但这还远远不够。而且这其中不乏优先级的问题。毕竟,重建博物馆和艺术中心(且不说在疫情期间还无法开放)的紧急性如何与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缺医少药的人们比较?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这种让他们寝食难安、没有指望的政治制度的终结?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以至于出现了认真要求法国重新殖民黎巴嫩的呼吁,而且有超过六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更重要的是,尽管最开始的努力令人振奋,但募资活动的复杂性对于这个地区的文化文作者而言并不陌生,在过去三十年里,他们都处于类似活动接收的一方,从1990年代灾难式的资本主义化到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再到阿拉伯之春漫长而悲伤的故事。现在是时候认真地提问,这种捐助是否真的可以让文化艺术组织变得更有可延续性,是否可以让民主更有希望,是否可以让知识分子更有能力去摧毁一个糟糕的政府并且开创新的可能性?这些基金从来没有带来可信度或者公正。在我愤世嫉俗的心中,这种紧急拨款无异于修修补补,只是把一切带回“正常”的手段——这也意味着让那些“sulta”继续掌握权力。如果说它取得了任何的进展,那就是革命至少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持续、坚定提问的时空:你和那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灾难是对系统的扰乱”,穆尼耶说,“不是去跟系统周旋,而是去破坏它。承认这里的一切都没有问题无疑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在去见穆尼耶的前一天,我和年轻作家埃德温·纳斯尔( Edwin Nasr)碰了个面,他很喜欢提一些尖锐的问题。无论在现实的交谈中还是在社交媒体上,他都抛出了一些关于募资活动及其共谋者——包括他自己,包括我,以及其他与我们一样从事文化艺术的人——技巧性的攻击性问题:哪些艺术家、作家、画廊家和设计师与导致黎巴嫩经济崩溃的主导者之间有关联?艺术单位是否应该对爆炸区域的士绅化负责——使得大批工薪阶层居民在爆炸前就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为什么外国酒吧老板可以在黎巴嫩申请丰厚的补助?纳斯尔提问的方式并不是那种哗众取宠式的,他十分小心,并且秉持着坚定的自我批判的精神。
贝鲁特仍处在Covid-19的封锁中。我们无处可去,所以纳斯尔和我只能在哈姆拉街一直绕圈子,这也让他处在一种反思的状态里。在革命中以及在爆炸后不久,有不少针对那些操着熟练英文、拿海外补助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框架里如鱼得水的艺术组织负责人的非议。这个城市里很多在海外知名的艺术组织都是从跟政府的极端对抗中开始的。或许他们还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思考他们自己生产出的那种权力。

或许接下来的几个月恰好是思考的时机。在地的工作已经转变了方向。黎巴嫩造型艺术协会(Ashkal Alwan)的窗户已经全碎了,管线也都爆裂,但他们开始为失去工作室的艺术家提供空间。该组织也将自己接下来的“居所工作空间项目”(Home Workspace Program)转向技术培训——在经济崩溃下的求生技巧。艺术家西伦·法图(Sirine Fattouh)为那些在爆炸中遭受心理创伤的孩子们组织了一个温馨的工作坊。乔玛娜·阿塞利(Joumana Asseily)的画廊Marfa(阿拉伯语的“港口”)离爆炸现场非常近,但他们也决定重新开张,出于对这片区域以及这里的人的热爱。贝鲁特艺术中心的前后门都炸飞了,但他们还是将全部空间让给NGO组织,用作仓库或者作为举办募款活动的场地。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充满希望的。人们主要的情绪还是愤怒。我听到人们谈起绳索、绞刑架和断头台。黎巴嫩造型艺术协会的创办人克莉丝汀·托姆(Christine Tohme)向来语言丰富有趣,她把黎巴嫩的政治阶层描述为暴虐和机会主义的,一群可耻的吸血鬼。我去拜访了艺术家组合哈利尔·乔雷吉(Khalil Joreige)和乔安娜·海吉托马斯(Joana Hadjithomas),发现他们正在整理工作室的残余物。(他们的公寓、办公室和电影制作公司都被毁掉了。)哈利尔靠着一件已经破掉的混凝土浇筑的作品说,“一般来说灾难总是一次带来一个问题,而不是同时来三个。而且我们甚至没法儿说这是场浩劫,因为那个系统还是没有被撼动。”真正的浩劫会摧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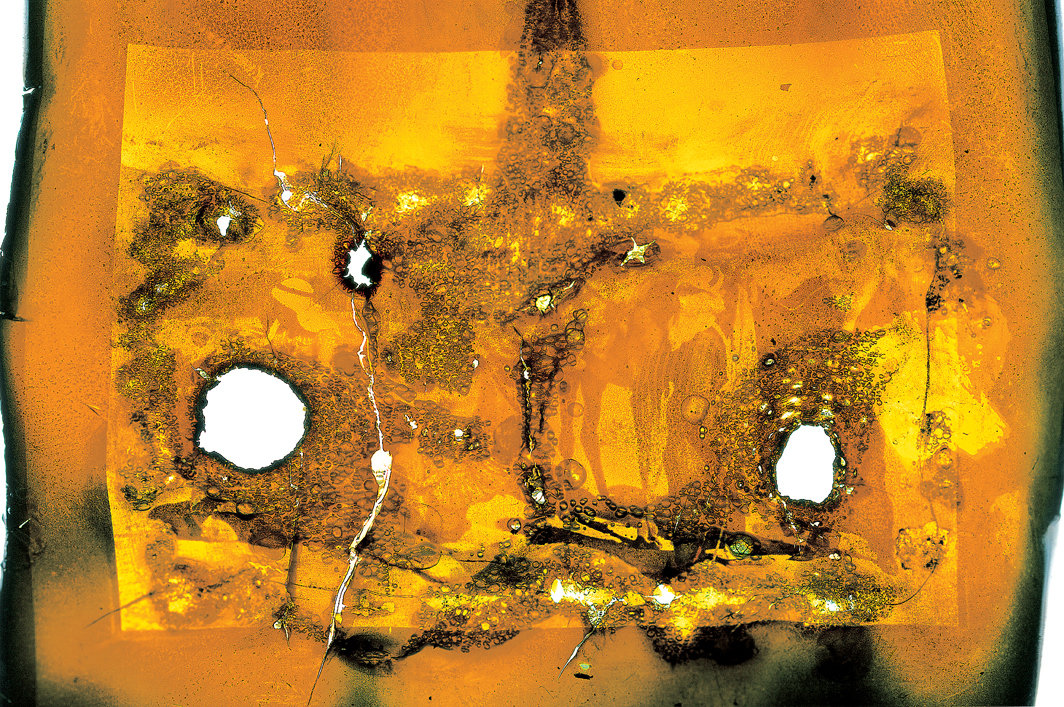
我在贝鲁特的最后几天,跟艺术家海格·艾瓦吉安(Haig Aivazian)聊了聊,他跟电影人艾哈迈德·戈森(Ahmad Ghossein)在今年一月一起接下了贝鲁特艺术中心负责人的位置。他谈起了他和其他人一起做的工作,关于机构应该如何行事以及艺术家可以做什么,我意识到两件事。我觉得十分自责,因为从2017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贝鲁特,此前的15年我都很稳定地生活在这里,我把我的孩子从这座我热爱的城市带离,想要给他们所谓更好的生活,我为我没有在这个城市经历艰难的时刻呆在这里感到自责,为我自己的毫发无伤感到自责。但更重要的是,在我自己的这些内心活动之外,我意识到贝鲁特对艺术的贡献从来都不在于空间或者收藏或者展览,也并非真的关于机构或者机构对资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以及这些钱是否真正起效。这座城市对艺术的贡献在于这里的艺术家们对自己、对彼此提出的艰巨的问题和随之而来艰苦的思考。
“最终空间都会消失的。”艾瓦吉安在谈到贝鲁特艺术中心时说。他说,机构真正拥有的是“他们所做的工作的记录。我们现在谈如何维系的时候,并不是在说机构的灵活性,而是在努力找到继续的方式,努力保持清醒,努力一起思考,一起写作,甚至仅仅是找到在一起的感觉,而不去问结果是什么。重要的不是在创作的艺术,而是人们是如何工作的,就好像其他职业一样。有一种与艺术相关的思维模式是有用的。艺术界热衷探讨的政治紧迫性可以被很好地利用。贝鲁特是一个检验全世界之弊病的超级实验场”,他补充道。“我并不喜欢这点,但我深陷其中。”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相对年轻)的记者的时候,那是贝鲁特战后重建的高潮时期,每当有机构要开发新的时髦地产项目时,总会因为挖掘到古迹而停摆。这是一切建立在自我的废墟上的古老城市的常态。那个时期,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让这个城市闻名于世的罗马法律学校的遗存物,那是在六世纪的地震之前,在查士丁尼一世的时代。“但是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发现”,萨米尔·卡西尔(Samir Kassir)在他讲述贝鲁特地方史的著作中说。“而且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所发现,因为罗马时期的教学系统或许与今日甚至中世纪的大学完全不同,并不需要自己的建筑。”法律学校说不定只是在一棵树下传道解惑。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播,思想的分享,人们如何聚集在一起思考。今日贝鲁特的文化艺术或许也是一样。或许空间终将消失,或许建筑再也不会恢复,或许一些机构就此消声觅迹。爆炸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思想却未因此消失。尽管未来还很艰难,统治者会倾尽全力消灭有损他们利益的一切,但这些思想有其属于自我的生命,它们会持续地对我们产生启发,让我们做得更好,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凯琳·威尔森-葛蒂(Kaelen Wilson-Goldie)是一位生活在纽约和贝鲁特的评论家。
文/ 凯琳·威尔森-葛蒂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