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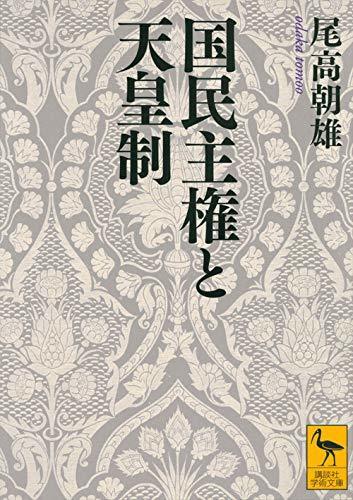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往往认为日本战后宪法改变了日本的“国体”:不仅主权归属从之前的的天皇变成了日本国民,并且天皇从握有统治权的政治主体变成了一个“象征”。战后宪法中包含着的国民主权与传统天皇制的张力,构成了日本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迄今为止面临的难题。
在诸多尝试调和“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努力中,尾高朝雄(1899-1956)出版于1953年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于今年明仁天皇退位的时间点上再版此书,其用心更是值得推敲。作为凯尔森(Hans Kelsen)、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尾高朝雄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理学,其《实定法秩序论》、《法哲学概论》等书都在出版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与上述法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作者试图在其中解决战后日本国体的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在日本,国体一语在表示法律或政治上的国家基本组织的同时,也用来表示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国民道德式的情谊、维系君民的国民精神上的一体感等等。不过,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国体也预设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如果没有上君治下民、下民敬上君,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不成立”(47页)。如果战后日本宪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那么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将随之发生剧变,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动荡。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出现,需要着手对战后日本的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进行讨论。而既然日本的国体据说向来是“以‘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为核心的国家结构的基本原理”(15),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日本的统治权或主权被归于天皇,尾高的着力点便在于“天皇主权”问题。尾高首先从“主权”在现代西方的兴起入手,指出博丹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得以诞生的历史背景:“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理论,即国家的力量超越封建诸侯的力量,也不输给天主教教会,也不服从于其他国家的意志。这就是‘主权’概念,主权‘至高性’的理论”(56页)。不过,在将“主权”概念还原到其诞生的历史背景之后,尾高宣布:如今这样一种至高的、不可分割的、由主权者意志的任意性决定的主权权力,在政治的意义上已经不合适了。“在今天,通行的公理恰恰是:主权决不是能够自由破坏国际法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就国内法而言,也可以说我们必须确认的根本原则是:主权决不是位于法律之上的最高绝对力量”(59)。
既然“主权”不再具有至高性,那么它必须服从于某项原则。这一原则在尾高这里的表述,就是“nomos”。关于希腊词“nomos”,学界的讨论可谓多矣;人们一般将它解释为“习俗、律法”等等。而根据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大地法》(1950)中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尾高发现“nomos”一词,恰恰是通过阅读施米特出版于1934年的《法律思维的三种类型》——“nomos”的原初含义是“占领、征用”,其后衍生出“分配”、“生产”等意思,直至发展为“法律”的意思。不过,由于尾高并没有读到《大地法》,他对于“nomos”的理解颇为直接,即“法的理念”:“‘nomos’这一希腊语的细节,现在我们不谈。在这里,我们将‘nomos’的意思理解为法或法的根本原理。这样解释的话,这个语词……可以说以令人印象最深的方式表现出:权力必须遵从法的理念。”(63页)。既然“必须说主权恰恰在于‘nomos’”(64页),那么无论具体的政治体制采取何种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须遵从“法的理念”这一根本原则。
不过,究竟什么是“法的理念”?尾高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只能说是泛泛而谈:所谓“法的理念”,便是“人的‘平等’。一切人的‘平等的福祉’”(70页)。然而,难道问题不恰恰在于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平等的福祉”吗?尾高放下这个问题不予追究,而是继续通过“法的理念”重新定义“国民主权”和“天皇制”的意义。从“国民主权”的角度而言,主权并不在于国民个体的总和,而在于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所谓的“公意”:“位于一切之上的国民公意已经不是现实的权力意志。它是一切权力意志必须服从的、恒常不易的正确性,总是正确的‘nomos’”(118页)。由于尾高将“公意”解释为“法的理念”,“国民主权”也就被翻译为“‘nomos’的主权”。
而从“天皇制”出发,尾高采取的策略是追究日本传统上自源赖朝以降数百年间的武家统治时期的“天皇制”性质。正因为天皇在此期间不具有实质上的权力,他才能作为“所有意义上超越政治实权”的存在而得到尊崇:
正因如此,天皇才能是不受政治瓜葛污染的神圣存在。与此相对,正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是现实的权力,其自身内部就没有客观正确的根据。因此,后者有必要从前者那里获得自身地位正确的根据。(131页)
天皇的这种类似“象征”的存在,被“万世一系”这一无法从字面意思上进行理解的统治口号概括。也就是说,在日本历史传统中,天皇的统治向来不是以现实政治权力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作为国民内心依靠的理念”出现,从而包含“总是正确”的含义(138页)。于是,“天皇的统治是一以贯之的理念”(141页),“国体”作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统治”,也就被重新解释为“理念的统治”。“天皇制”于是成为“理念统治”的代称。

可以看到,一旦从“法的理念”的角度重新解释“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两者的关系就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紧张,因为主权的落脚点如今既不是在国民个体身上(也不是在具体的国民集合体身上),也不是在作为具体个人存在的天皇身上,而是在同时体现于国民之“公意”和天皇之“万世一系”之上的“法的理念”。“国民”或“天皇”成为这一理念的不同表述,甚至作为国民统一性之“象征”而存在的战后天皇,能更好地服务于“理念之表述”这一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尾高尤其将自己的论述与所谓“天皇机关说”区分开来:根据他的论述,后者尽管将天皇还原为一个国家机关,但国家机关说在西方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一学说是君主与民众之间相互拉锯和妥协的产物。与之相对,“法的理念”不允许、也不需要任何妥协,因为“国民主权”和“天皇制”在遵从“法的理念”的层面别无二致。
不过,尾高通过“法的理念”而统合“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之后,也指出了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国民主权”与明治宪法的“天皇统治权”之间的重大差别:简言之,后者的天皇统治在现实上带来的结果是,如丸山真男所说,整个日本社会朝野——无论是制定和执行决策的政府,还是听从指挥的战士,乃至一般日本国民——都陷入一种“无责任”的体制之中。政治责任被让渡给天皇,而后者统治的正当性又被一种神话般的“万世一系”理论加以审美化、神秘化。对此,尾高指出,必须认识到“天皇统治中追求正确之理念的,恰恰是国民自身,除国民之外别无他者。(中略)受到尊崇的,其实是国民自己的内心”(152页)。因此,将“主权”从天皇转移到国民“公意”这里,会有助于国民树立起政治责任心,承担对于公共事务的职责。
既然“主权在君”或“主权在民”的区别,被尾高置换为同样处于“法的理念”下的两种政府形式的差别,那么“国体”的问题就被还原为“治理”的问题。相较于君主凭借个人意志在现实政治事务上做出决断的体制,一个由多数民众投票决定政策结果的体制无疑能让国民更切实地承担起自身的政治责任。在尾高看来,“主权在国民,这是民主主义的理念层面;采用议会多数决定作为把握正确的国民公意的方法,这是民主主义的现实层面”(123页)。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是‘数量的政治’。如果民主主义否定了多数决定原理,这就肯定不是民主主义”(182页)。
说到这里,作者对于战后宪法中处于紧张关系的“国民主权”和“天皇制”的调和便接近尾声了。不过,这样一种调和的尝试本身,或许恰恰可以被读作战后日本国体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症候;换句话说,尾高的著作所遮蔽的问题,远远要比它试图解决的、宪法层面上的“主权归属”问题深刻得多。尾高这本《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出版,引起了同为东京大学教授的宪法学家宫泽俊义的批判,两人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论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宫泽的一篇文章中,尾高承认,宫泽就“nomos”提出的尖锐问题——究竟由谁来决定“nomos”的具体内容——触及到了主权问题的核心,而这是《国民主权与天皇制》所未能解答的:“决定什么是‘nomos’并由此立法的,是君主那样有着特定身份的人,还是非特定的国民,必须要二者择一。宫泽教授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203页)。不过,尾高坚持认为,自己所谈论的不是主权的权力归属,不是主权的内容,而是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的“根本原则”,即作为“法的理念”的“nomos”所要求的“一切人的平等的福祉”。换句话说,在尾高看来,重要的不是谁来规定“nomos”,而是在现实政治处境中谁来执行“nomos”的要求——后者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民主政治的议会多数原则。
这里的问题是,《国民主权与天皇制》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美国占领军的存在,更没有提及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对于战后宪法制定工作的直接介入。在尾高调和国民主权和天皇统治传统的尝试中,美国似乎是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尽管在加藤典洋等论者看来,恰恰是这一因素构成了日本战后社会的“扭曲”构造。然而,就在讨论战后宪法的成立过程时,尾高的论述表明,“nomos”的根本原则恐怕既无法在理念上还原到国民的“公意”,也无法在实际上还原到议会的多数决定:
币原重喜郎内阁发表与明治宪法在表面上根本不同的《宪法改正草案纲要》时,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此意外之事十分惊讶。(中略)让国民感到惊讶的《纲要》之后成为《帝国宪法改正案》,由第一次吉田茂内阁向第九十次帝国议会提出,仅仅进行了一些修改,便成为《日本国宪法》。的确,这是根据“正当选举出的国会”的国民代表的多数决定而成立的宪法。不过,如果单单凭借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仅凭当时处于虚脱状态的日本国民的力量,究竟能否制定出像这样的民主主义宪法,不得不说是十分可疑的事情。(210-11页)
国民与议会代表之间的脱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毋宁说这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常态。问题在于,在制宪的关键时刻,在“法的理念”既无法通过传统的天皇制得到体现,也无法通过其后宪法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得到体现的“间隙”——这个“间隙”同时也是日本国体发生变革的“间隙”——恰恰是美国代替日本国民而体现了“法的理念”。那么,按照尾高的逻辑,是否可以说GHQ同样根据“nomos”的根本原则行事,因此与“国民主权”或“天皇制”没有本质区别?GHQ规定什么是“一切人的平等福祉”,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甚至强行要求日本政府通过一份理念先进的宪法——这一切是否无损于日本的“国体”?一百多年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已经在充满危机感的《文明论概略》中给出了答案:国家被外国人占领,这就是国体的破坏。只要美国有权就“nomos”的内容做出规定,甚至有权规定何种生活方式是好的、何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的确可以说“国民主权”和“天皇制”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表面的——但这不是因为两者都遵从“法的理念”,而是因为两者都必须遵从美国。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