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星野太,《食客论》,讲谈社,2023,272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我不擅长与他人共同生活。”这是批评家星野太(Hoshino Futoshi)在其近著《食客论》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奇特的开场白明确地提示了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共生”或“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不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视为一种理想或价值,也指向对于种种社会歧视、不公和不平等的消除,包含着对于所谓“求同存异”乃至“互惠互利”的追求;然而,这种将“共生”视为理想的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单独生存。换言之,“共生与其说是高迈的理想,它首先是我们无法抵抗的现实”。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他者——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乃至病毒——共同生存。“如果要围绕共生来提问的话,那么必须提出的疑问句是:如何共生?”
如何共生——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它涉及的首先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无法摆脱的现状: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者的共存状态之中,准确勾勒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如何共生”这个问题被星野翻译为“食客”的问题。
这里所谓“食客”,意思不是当今中文语境中泛指的吃东西的人,而更接近于古汉语中的“门客”,即寄宿或寄食在他人家中的人。作者认为,“食客”可以对应于希腊语中的parasitos,本意是“在旁边吃东西的人”,而后者进一步演化出“寄生”(parasite)一词。“在旁边(para)吃别人家的餐桌上提供的食物(sitos)”,构成了“食客”的一个原初和基本的形象。星野在书中通过“食客”这一关键词,串联了一系列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文本,包括罗兰·巴特、九鬼周造、梅尔维尔、汉娜·阿伦特、傅里叶、石原吉郎、琉善等等。由于这些章节原本是刊登于《群像》杂志上的一系列连载,因而从风格上来看,可以说这些视角独特的阐释本身就像是位于文本“旁边”的一些“食客”般的阅读——重要的不是(例如)作者的阐释或类比是否妥当;而是看到他如何通过这些关联松散的文本勾勒出一种独特的存在,并以此介入“共生”或“共存”的问题。
首先,作者对于“食客”的界定如下:
位于作为能够被认识的他者的“朋友”和“敌人”的旁边,那个不可见的同行者。……这个最一般的名称——有时它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寄食者”,有时则是包含非人的“寄生虫”在内——在英语中叫“parasite”,它是本书的主角。(第26-27页)
因此,关于“食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寄生”的问题。的确,乍看起来,“寄生”一词所包含的寄生者与宿主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宿主在时间和地位上都优先于寄生者——似乎也可以运用于食客和主人之间的关系:食客并不属于主人的家庭成员,而往往是以自己的智慧和言辞博得主人的信任或喜爱,从而谋得一餐一食。不过,星野将食客的这种“寄生”状态扩展为我们每个人的本体论状况:
我在这里以“寄生”这个词来指涉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现实,即字面意义上不依赖于其他生命就无法存活的现实。或者更直接地说,也可以称之为“自足生命”的不可能性。我们当下想要做的,就是将脍炙人口的“共—生(co-existence)”的范式,转换为以新面貌呈现的“寄—生(para-existence)”的范式。(第80页)
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视角转换,同时也是一种带有伦理意义的决定,因为一旦将我们每个人的生存视为非自足的、依赖于其他未必被我们意识或认知的生命,那么既有的基于“自我”、“主体”、“自律”等概念的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必须得到重新界定。于是,对作者而言,对于食客和寄生的关注,必然要求我们暂时离开自身所处的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认知模式和秩序,将事先被排除在外、然而对我们的生存而言不可或缺的各种“他者”重新放进“共生”的视野之中——不是为了理想化这种“共生”或“共存”,而是为了借助它们来让看似稳定的、习以为常的、似乎不证自明的秩序发生动摇:
我们始终被无数的存在者包围着。然而,通常成为认识对象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将他者予以认识,归根结底是与这一对象共有某种利害的时候。因此,在日常最为松散的认识中,无数的他者被还原为“朋友”或“敌人”。当从这种认识网眼中逃脱的“随便怎样的东西”突然变得无法忽视的时候,它就开始带上“食客”的样貌。(第188页)
换句话说,作者认为,我们通常对于“他者”的认识,总是已经将“他者”还原为某种价值明确的范畴——无疑这里的“朋友”和“敌人”的二元对立来自卡尔·施米特在界定政治的概念时做出的“敌友之分”。事实上,我们不必拘泥于星野的这一论断的字面意思,毕竟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松散认识”中,并不真的会简单地把“无数的他者”都“还原为‘朋友’或‘敌人’”。星野想要强调的与其说是不属于“敌友之分”这一特定对立结构的“他者”,不如说是那些无法被积极明确的认知结构和框架所把握的存在者:“寄生者是所有具备下述潜能的存在者的名称,它们打乱了习惯性法律所带来的共有规范,给这些规范造成决定性的变化”。
因此,“非敌非友”仅仅是一个例子;同样,在分析“食客”、“哲人”和“智术师”这三者的关系时,星野写道:
既不是拥有丰富知识、恣意操弄语言的贤人,又不是教育家或雄辩家,而仅仅是在主人旁边索要食物的人——拥有如此背景的食客,恰恰是横向突破了哲人与智术师之对立的“第三者”。(第85页)
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既不是哲人也不是智术师,既不构成共同体的内部,也不属于共同体的外部——在作者看来,食客的这种不属于任何范畴的“可疑的存在”,对既定的秩序、结构、认知模式、身份、价值体系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同时这种挑战又不会凝结为某种积极明确的、实证意义上的替代性秩序或身份同一性,而始终以“寄生”的方式存在于“旁边”。难怪作者在整本书的最后部分,会指出“食客”和“幽灵”形象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正是在食客的这种“既非A亦非B”的句法那里,《食客论》的论述包含了一种微妙却关键的歧义性。这种歧义性涉及到我们与食客之间是否具备沟通可能性的问题。
第一,食客可以是一种具备“可沟通性”的“中间性的存在”。举例而言,星野通过考察西塞罗的《论义务》和施米特的《海盗行为的概念》(1937)指出,“海盗”作为不遵从任何法律和义务的存在者,恰恰是一种缺乏明确界定的身份,“在‘缺乏信义’这一点上,我们随时都可能‘成为海盗’。并且,这种海盗不是大海彼岸飘荡着的‘绝对他者’,而是以我们身边的‘中间性的他者’形象现身”。相对于哲人和智术师的食客形象,无疑也属于这种“中间性的他者”。
然而,无论是海盗还是食客,他们的“中间性”事实上并未颠覆既有的价值体系或意义结构,反而显示了后者独特的经济或配置(economy)——例如,在施米特笔下,海盗照亮了海洋和陆地的两种普遍秩序,而在食客与主人的关系那里,两者并不是通过款待或帮助,相反是通过话语和食物之间的某种交换或交易联系起来的。
换言之,尽管这种食客无法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如作者所说,否则他们就“丧失了作为寄生者的存在样态”),但是,他们和共同体的成员之间仍然保持着一种“可沟通性”;非但如此,这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可沟通性”可以说正是借助食客的形象得到了鲜明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将食客类比为“幽灵”之后,星野恰恰通过援引梅尔维尔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巴托比”的形象而否定了这种类比,因为“幽灵”作为“食客”“实在是太过了”。与之相比,巴托比这个“权利上确实可以将他赶走,但事实上又不可能”的形象,在作者看来更符合“‘寄生式’存在”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星野对于食客的考察,其实揭示的是共同体建立其上的那个排除机制——即通过“排斥性的包含”(阿甘本)而将貌似处于意义系统之外的“他者”(无论它是“海盗”还是“门客”)予以驯化和收编。于是,“中间性的存在”的说法就颇有症候意味:它表明食客其实总是已经处在共同体的拓扑学结构之中。
第二,与之相对,食客也可以是一种不具备“可沟通性”的“他者”。很显然,例如“寄生虫”或病毒便是这样一种依附于其他生命之上、却无法产生任何交流的食客。对于这种食客的认知,往往不会揭示共同体的基础,更不会动摇、甚至反而会强化既有的秩序和价值体系——过去几年内,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应对Covid-19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和方式,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就此而言,寄生虫或病毒一方面模糊了共同体的内外边界,另一方面却称不上是“中间性的存在”,而更接近于“绝对的他者”。在此,我们无需任何政治或文化理论就能知道,古往今来,通过辨认一个威胁性的他者(无论它是否是同类),共同体成员得以强化和巩固自己的集体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歧义性源于“食客”一词的字面含义和隐喻含义;然而,在《食客论》中,这两种含义似乎展现出同一种构造,即相对于“主体=主人=宿主”的依附性、边缘性的存在。例如,在下面一段话中,作者意味深长地涉及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食客:
非常明确的是,食客被严格排除在可以共同享有餐桌的“家人”或“朋友”等范畴之外。寄生虫在我们体内摄取营养,但我们并不是和虫子们“共同”吃饭。在旅途中得到一宿一食之恩的行旅者,并不是交杯换盏而成为正式“家人”的人,而是又将去向别处的“客人”而已。(第218页)
的确,我们并不和寄生虫“共同”吃饭,也许我们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和偶然在家里寄宿的客人(但“客人”这个语词也已经相当可疑)“共同”吃饭。问题在于,尽管“我不和背包客共同吃饭”与“我不和寄生虫共同吃饭”在语法上是等价的,但除非是修辞上的用法,不然我们显然无法通过语法上的等价而将背包客和寄生虫都还原为同一个范畴,即“食客”。或者说,与“门客”相对的“我”和与“寄生虫”相对的“我”,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如何与动物共存”意味着生态保护的诉求,而“如何与病毒共存”则意味着针对性的卫生措施、治理方式乃至话语策略。

“食客”一词带有的这种再明显不过的歧义性,不可能不被作者意识到。因此,指出这一歧义性不是为了批评《食客论》的某种大而化之的缺点,而是为了进一步追问:星野为什么要在如此宽泛乃至宏大的层面上探讨“食客”?
如前文所述,无论属于哪一种含义,食客最终都不像作者认为的那样,对既有的价值体系或意义结构构成颠覆或挑战,反而形成了一种补充或强化。在我看来,作者想要强调的、作为威胁和挑战的食客,恰恰来自某种位于上述歧义性“之间”的、无法被归类的“幽灵”形象。但我们不必诉诸“幽灵”这个夸张的表述;因为从结论来说,这种食客既不是门客,也不是寄生虫,而不外乎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打交道的“他人”。换言之,一般而言的“人际关系”,在获得政治含义之前的“人际关系”(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才是《食客论》的根本关切。此话怎讲?
在一个关键段落中,星野借助“寄生虫”和“宿主”的隐喻写道:
我和周围各种东西之间的关系,绝不应该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残酷关系。就像食客对待宿主那样,我与他者的关系始终受到下述关切的支撑,即不要让一方消灭另一方。我们与他者之间存在着无限微妙的细微差别,不可能完全收编到生物之间无情的捕食关系中去。如果用比喻的语言来说,这不是一种相互间自始至终性命攸关的“口腔关系”,而是通过彼此口唇来轻轻咬合的“口唇关系”。(第141页)
毫无疑问,这种“口唇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寄生虫和宿主之间的关系,尽管寄生虫的确会随着宿主的死亡而死亡。相互间通过口唇来轻轻咬合——这非常接近对于亲吻的描述;然而,作者明确将“关于性爱的讨论暂时排除在外”。为什么?尽管作者对此没有阐述,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性爱关系或恋人关系预设了双方的对称性,而与食客所包含的根本的非对称性相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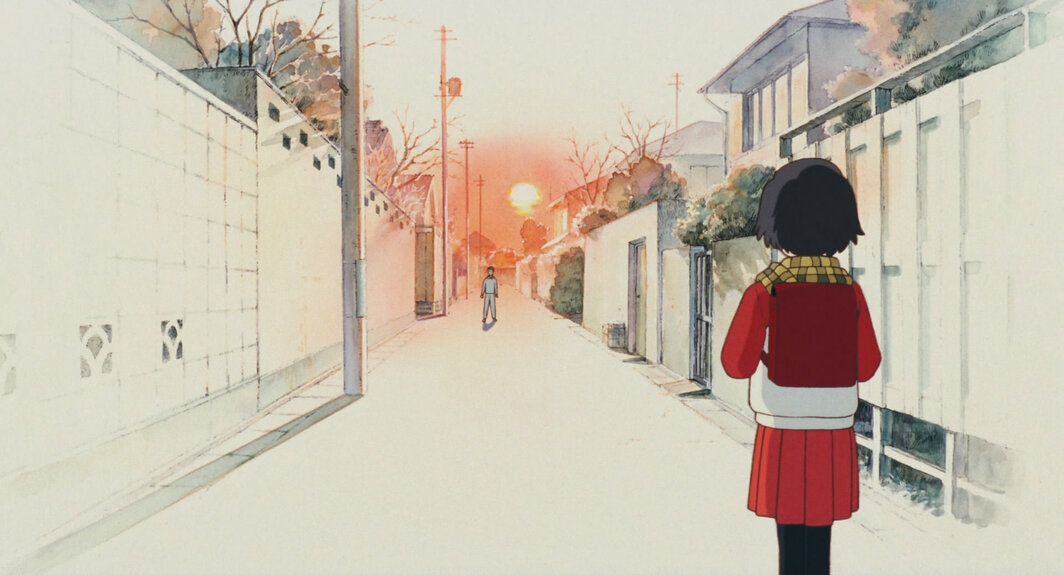
于是,无论是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关系,还是“通过彼此口唇来轻轻咬合的‘口唇关系’”,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关乎非对称的人际关系的隐喻。这种“非对称的人际关系”指的不是(例如)社会分工意义上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近乎无法挽回、无法言明的、注定要从我们的认识中逃脱的关系。星野在讨论诗人石原吉郎时写下的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他所关切的这种非对称关系:
“我”确实和“你”相遇了。但是,我们也许至死都未能真正地理解彼此。或者说,在“我”周围,也许存在着现实上没有相遇、但在更深层之处已然相遇的“你”。(第210页)
不难理解的是,作者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也借助“寄生”的隐喻而将这种关系翻译为寄生者和被寄生者之间不断转换的非固定、非对称关系——某个作为“宿主”存在的生物,同时也可能寄生于另一个生命之上等等,由此形成一个“连锁的寄食结构”。也许这就是星野所谓的“‘寄—生’的范式”。不过,重复一遍,重要的并非这一带有本体论色彩的论述本身,而是作者借助“食客”这一歧义性语词,将“可沟通性”乃至“人际关系”从后者所预设的“个体性”、“主体性”、“意愿”、“意识”、“责任”等概念那里抽离出来,为“构想新的共同体形态”做好准备。同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理解作者为何要大而化之地将“食客”和“共同体”对峙起来: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可沟通性”,将不以共同体的意义结构或身份认同为前提,甚至不以理性或意志为前提——在共同体之外,或者说,在属于共同体内部的无法认知的“外部”,我们与他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换始终已经在进行之中。这不需要我们下降到微生物的层面才能理解;事实上,这或许从来就是我们和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之一。
王钦,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他的最新著作『魯迅を読もう: 〈他者〉を求めて』于2022年由日本春秋社出版。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