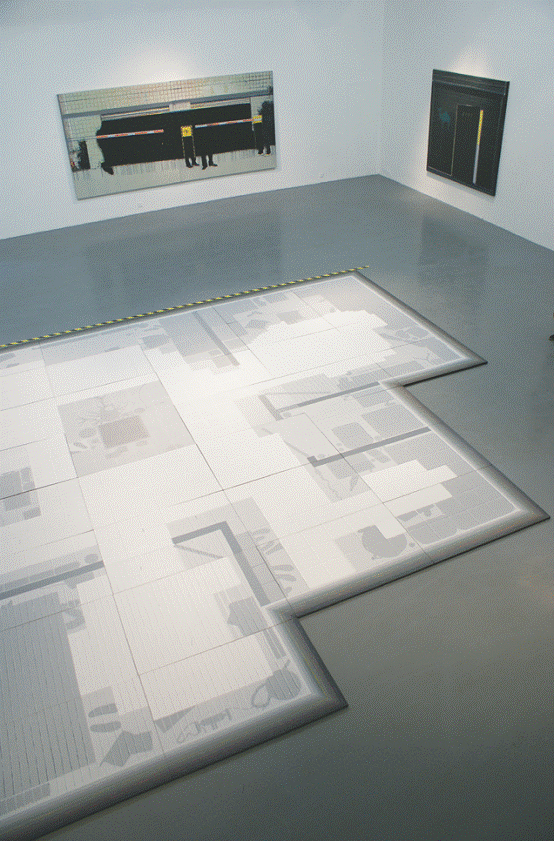庄辉
几个甘肃和青海牧区风格的帐篷占据了常青画廊高挑的大展厅,墙上列有两个省份的若干地名,彼此间由线条连接,标示出某种旅行路径。观众很快就会发现,策展人凯伦·史密斯试图在画廊空间里营造出一种场景,以便观众能够以艺术家行走期间的视角进入展览。过去十年,庄辉每年都会花几个月进入祁连山区,旅行中的创作先后催生了两个展览(其中之一是我本人于2017年在同一家画廊策划的“庄辉:祁连山系”)。在这次最新的展览上,每座帐篷里都播放着不同的视频,画面中,庄辉在山野间完成着各种看似徒劳的动作,比如尝试用木棍撬动巨石,或者从河床上捡起石头,端详一番又扔回去。另一些艺术家与风景之间的互动则更为诗意,比如在山坡上沿着另一个山坡投下的阴影边缘行走,或者搬起一块石头从镜头后走到镜头前,最后渐渐走远,在灰黑的土层上留下一串赭红色的脚印。
而在放置于二楼展厅其中一个小空间、由不同形状和尺寸的投影组成的录像装置中,我们看到艺术家赤身露体行走于一片奇异的风景,手里拿着一面锣,一边走一边敲。锣的声音和庄辉身体的运动所传达的语言似乎除了与风景对话之外,再无其他目的。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空间里,在铺设有一层细沙的地板上摆放着两类球状物体。一类是用从祁连山脉收集来的石头所制,另一类是以唐三彩工艺制作的陶瓷品,后者是庄辉让工匠按照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尽量模仿石头纹路烧制出来的产物。瓷球看起来富有当代感的颜色和纹样完全出自传统工匠之手,艺术家并未干涉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