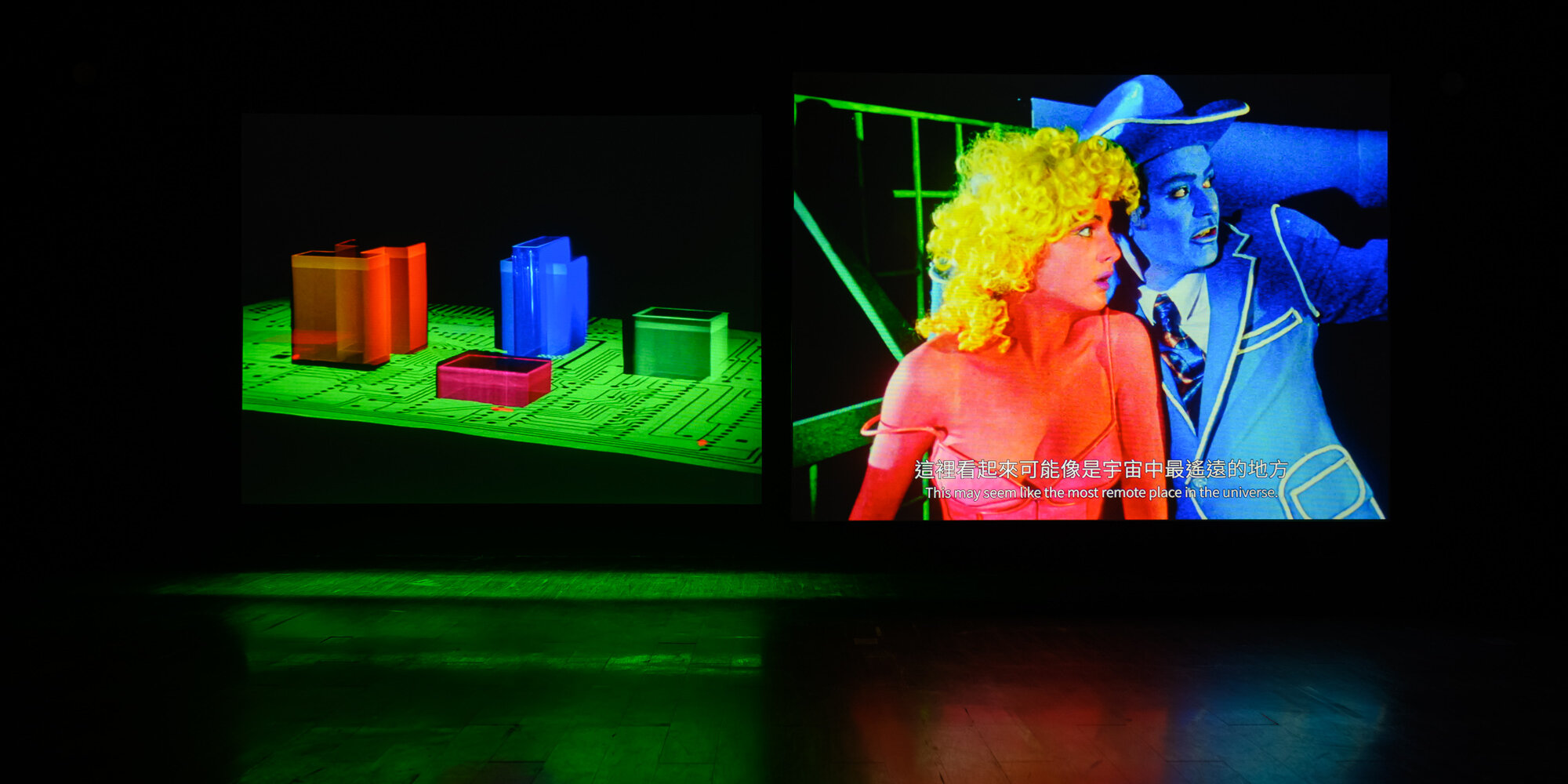日惹双年展的观看偏移练习
如果你去一个双年展,最靠谱的不是展墙、不是动线,而是城市中每天五次准时响起的宣礼声和街头巷尾从未缺席的猫,那大概就是在日惹了。展馆资讯拼拼凑凑、活动安排随时更动,观众靠口耳相传才能确认今天到底有什么在发生。很快你会意识到:在一个仍维持苏丹制度的环境里,双年展只是被嵌入一套更古老、更具韧性的社会节奏之中的一段短暂时间。
这种边走边定义自身位置的状态呼应了爪哇语“KAWRUH:Tanah Lelaku”——第十八届日惹双年展的主题。Tanah是脚踏着的土地;Lelaku是落地、行走、重新尝试;KAWRUH在二者之间往返,一种还在生成中的知识。如果说这种从土地与经验中生长的状态可以理解为“扎根实践之地”,那么对来访者而言,在错位与等待间,“扎根”首先意味着识别另一套运行法制——允许天气、信仰与人际关系主导行动,而非根据表定行程。于是问题也随之转向:我们能否接受双年展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作品的暂时集中?
看到卡瓦彦·德·居亚(Kawayan de Guia )的《M.O.M.A.(片刻的口述冥想档案)》(M.O.M.A [Momentary Oral Meditation Archives]),你可能会想到纽约的那个现代美术馆,但艺术家所做的似乎是把博物馆丢进搅拌机。毛坯房被铺天盖地的小画占据,听说这里未来会规划成超市,墙未刷完,地面冒灰,如果你还抱持“标准”的观展期待来,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