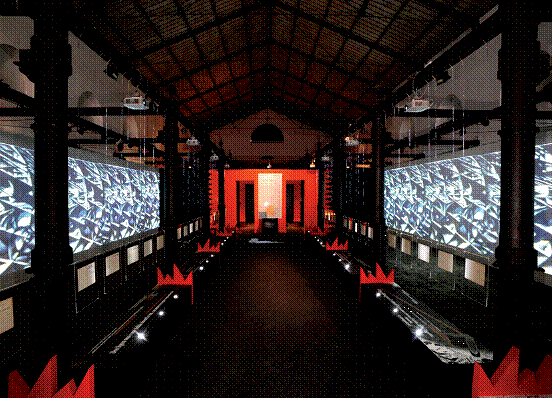
未来主义百年展
在过去的二月份,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刚刚过了一百岁的生日,但大西洋这一岸,却几乎无人对此进行欢呼,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当然研讨会,新的出版物,以及有关宣言的零星文字还是有的,而今秋的Performa也将献给百年庆;不过,除了纽约MoMA教育和研究楼地下室的一系列橱窗以及蒙特利尔加拿大建筑中心和迈阿密海岸Wolfsonian-Florida国际大学组织的《速度极限》展外,北美博物馆前沿的沉默令人纳罕,尤其是想到未来主义对历史先锋的重要性,这种无动于衷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说起来,似乎又情有可原:因为未来主义本来就是要捣毁博物馆—一个他们视之为当代艺术毒瘤的机构。无论是知识上、意识形态上还是实际的原因,眼下的这种沉默(例如,对于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宣言毫无耐心,对于其通过战争和对女人的鄙视来净化社会而感到反感,很多最好的图片已经被借用出去)与另一畔的欧洲大陆的热热闹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一年的时间里,都在为之举行着百年庆祝活动。
在米兰,罗马,罗维雷托, 重要的百年展已经开幕,其他的还有在威尼斯,柏林,巴黎和伦敦的。大多数展览都出版了学术性的画册,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犀利,夹杂着不同的声音,人们如圣徒祭祀般纷纷来到了现场。那些活动,就如那场运动本身一样,都蔓延到了大街上:为了纪念未来主义对于机械化运输的热情,一辆“未来电车”在今春穿过了米兰的大街,而这场运动对厨房的渗透也造访了罗马的Taver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