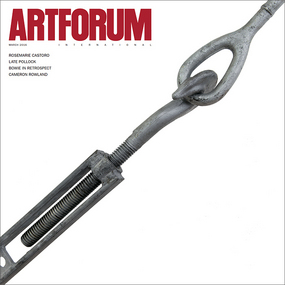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里,你最喜欢谁?这就难说了。Ziggy太容易—也许是“出卖世界的男人”或“瘦瘦的白公爵”?当然,所有这些人物都紧密关联于具体的歌词和音乐,关联于它们自己的时代和地点:柏林、伦敦、洛杉矶、巴厘岛(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将撒落在巴厘岛)。作为一个群体(遗憾的是,该群体的阵容现在已经固定),这些人物假面确定了大卫·鲍伊职业生涯的节奏,而他的粉丝们也可以追忆每个形象出现时,自己处在生命的哪个节点上。我们应该都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被他奇怪的声音迷住,各种原本不可能组合到一起的声音与单词居然构成了一首曲子,让人为之沉醉。鲍伊的作品进入我的个人生活是在七十年代早期,是姐姐介绍给我听的。我立刻变成了大卫的粉丝。那时候,姐姐还没有组建她的第一个异性恋家庭,更不用说第二个同性恋家庭了。我们都还是小孩儿,而姐姐有一台小小的唱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立体声耳机。现在回想起来,用密闭耳机左右声道循环聆听鲍伊的专辑—《Hunky Dory》(1971)、《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1972)、《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1970)—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
我第一次和大卫本人的接触就像一场高能冲击,媒体、音乐、名人光环的魔力全开。他就像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神话世界,因此你不会觉得他完全存在于跟普通人相同的空间里。当然,这些都是我脑子里的印象,而我当时的反应则充分表现了流行文化的癔症。这个我一直满心崇拜听他的音乐,关注他一举一动的传奇巨星现在居然真人驾临我的工作室。要协调幻想与肉身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难。后来我发现,这是大卫在场造成的一种普遍效应,有时甚至会招来令人捧腹的结果。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卫及其夫人伊曼,还有艺术家琳达·珀斯特(Linda Post)去MoMA看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展。大卫一边悠闲地漫步于展场,一边滔滔不绝地讨论艺术,仿佛我们身处某个结界当中,而周围所有人目光的焦点都早已从艺术转到他身上。最后,当我们准备离开美术馆时,一群女的围过来,开始摸他,就像陷入了一场突发的追星热病。
那是九十年代末,我们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友谊才刚刚开始。当时我住在下东区律路街175号的一间破旧简陋的工作室。大卫第一次到访时,我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让心情恢复平静。现在看来,巨星光环背后的他几乎就是一个正常人。除了一点以外:他是大卫·鲍伊,两个眼珠颜色不一样,有那样的嗓音。我依旧记得我们第一次对话的一些零星片段:我们都从自身经验切实感到毒品不可取。他在一边呷着咖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天南海北地从音乐聊到电影,聊到书籍、艺术史、漫画,再聊回音乐(很像他的职业生涯轨迹)。他对自身成就态度十分谦虚(说自己的作品是“从一堆屎里总能拣出几颗胡椒粒”),而他的幽默则让人难以忘怀,还有他深沉的笑声,常常伴随着狡黠的笑纹。朋友问我他为什么来我的工作室,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认识到,他喜欢艺术,喜欢讨论艺术创作,也喜欢亲眼去看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结果,大卫是想把我的一些作品用到他自己的创作中去。我们合作的大部分内容最后都对外公开发表了—网上可以找到大部分视频—但也有一些东西从来没有公开过。
所有艺术家都想当摇滚明星,而所有摇滚明星都想当艺术家。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很多搞音乐的其实都是未出柜的画家。我一直想给他们做一场展览,也曾经玩笑似地跟大卫提起过,尽管最好还是让这个计划停留在想法阶段。大卫知道没人会把他的绘画和装置作品当真,但它们看上去还是很不一样,对他而言,做作品就像跟艺术界日常互动的一部分,和访问工作室、参观美术馆或阅读艺术史差不多。正如他还醉心于很多其他形式,与艺术界的接触同样助长了他对创作过程的强烈兴趣,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为他自身创作提供了营养。大卫很少谈论自己的创作过程,但多年交往下来,我差不多能有些理解。他喜欢杰奎琳·汉弗莱斯(Jacqueline Humphries)的作品,有一次,他、我,还有Corinne “Coco” Schwab(大卫多年的朋友和私人助理)去访问汉弗莱斯的工作室,当我们都沐浴在汉弗莱斯作品银色表面的光芒中时,我留意到大卫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陷入沉思。我问他对作品构图有何感想。他的回答迅速而又明确:“很像我对音乐架构的想法。样式的重叠,刮掉一层,露出另一层。”“画的还是写出来的?”我问。“我的脑子里能看到,”他回答。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一直对流行音乐的某种能力十分着迷并深感嫉妒,那就是:流行乐可以用完全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材料—和弦进行、白痴也能看懂的歌词—为其赋予让人欣喜沉醉的力量。声音直接进入大脑,消失于无形,只在神经系统留下痕迹。简单直接,全民免费,也许音乐才是最伟大、最具平等性的艺术形式。它几乎提供了一种完美的模式,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常常思考艺术是否也能解开同样的难题。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被吸收到了摇滚乐里?实验电影又是在什么时候被音乐录像吞没和消化的?我这代艺术家对跨界的概念持有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我们相信借此可以脱离白立方的精英主义,进入其他媒介和领域:录像、表演、声音、音乐。前几代英国人抱有同样的想法—也许艺术界还没能认识到他们的作品也是艺术?大卫心脏病发作之后一段时间非常安静,直到有一天他跟我汇报说,他现在基本上一天看完一本书;他向我推荐了一本追踪奥利弗·克伦威尔头颅去向的书,克伦威尔死后,尸身被掘出来重新砍头,砍下的头颅从此开始流落四方。我很感激能够跟我的朋友大卫做这类讨论,有时候当他觉得谈话开始变得过于高级时,就会微笑着说,“不过是rock ’n’ roll而已。”
将来,鲍伊的作品会不会被视为某种“总体艺术”?我倾向于认为,当他2003年录制Jonathan Richman写的歌“巴勃罗·毕加索”时,就已经在尝试这种想法。歌词提醒我们,毕加索“从来没被人叫过混蛋”—而其贯穿一生的多产恐怕只有鲍伊可以与之媲美。我见到他时,他正在drum-and-bass上小试牛刀,穿着Alexander McQueen上台演出—我觉得那算是他创作生涯的后期阶段。年过四十的他身后已经有一段庞大而复杂多彩的历史。我记得有人认为他作为一名流行乐巨星来说太老,现在正在蹚成年人娱乐这趟浑水。但相对于所谓“27俱乐部”冻结的青春之泉,鲍伊的后期创作产出了海量材料—最后一共制作了近27张录音棚专辑。他是一位争议人物,在文化战争中久经沙场。外界关于他性别取向的无休止提问让他非常困扰,最后他干脆拒绝接受采访,让作品自己说话。
二十世纪初,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提出被他称之为“双重复现”(dédoublement)的说法,作为两种意识或人格同时并存于一个病人身上的例证。从那时候起,一直到八十年代多重人格障碍这一歇斯底里的流行文化现象,主体的分裂一直带有负面意味,在心理分析的领域里通常与创伤、虐待和被压抑的记忆有关。然而,作为娱乐,人们始终对其抱有强烈的兴趣(从化身博士到《三面夏娃》),并且借助从电视到Twitter等最新媒体技术持续对其进行探寻。
有人指出,这种建构另类身份的冲动有可能为另一种脱离弗洛伊德原型的意识提供模板。有一次在参观鲁宾美术馆时,大卫和我讨论了卡尔·荣格的《红书》以及荣格对艺术创作期间不同人物性格切换的另类观点。该想法明显区别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在我看来,鲍伊收集的不同人格面具正好提供了此类解放性轨道的绝佳例证,同时也向无教养的个人主义和固化的“真实”身份这一美式老生常谈指出了另一种选择。我相信,大卫搬到美国,部分原因是对英国阶级体系的反感,而美国这边的清教色彩也让他吃惊不小。对他而言,自我更新本来就指向未来主义,与之关联的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自我。他的作品既暗示了看似无限的可能性,同时又解构了自我表现的机制。几样道具,油彩妆容,一两道灯光;大卫就这样变幻出无穷的选项,邀请我们加入游戏。他是少数作品真正能成为局外人避难所的艺术家之一;通过某种神秘、即兴的化学反应,这些作品同时也滋养了其他艺术家。
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是一名现居纽约的艺术家。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