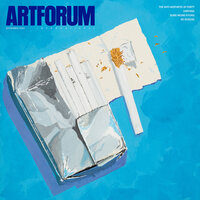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概念曾经对艺术和思想造成强力的刺激;如今它却像某种刚成过去的欲望冷却剂,让人兴致全无。在某些方面,后现代主义看起来比现代主义更像历史,因为后者在殖民主义、离散群体和全球性等问题的冲击下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正因其已不当季,如今反而成了一个回顾后现代主义的绝佳时机,哪怕回顾只是为了丈量我们与它之间的距离。
四十年前,由我编辑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出版;没多久,由布莱恩·沃利斯(Brian Wallis)编辑的《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重思再现》(Art After Modernism: Rethinking Representation, 1984)跟着问世。尽管学院出版社很快推出了同类文集,但最早的这两本书一本是独立出版社(Bay Press)出的,一本是当代艺术博物馆(新美术馆)出的。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不是在学院里孵化的,尽管它后来栖身于学院;同样,它也不是记者和宣发人员一拍脑门儿想出来的,即便后来它服务于文化产业。
与我们自由至上主义的当下相比,1980年代初虽然还不至于那么虚无,但依然是一个深刻反动的时期。随着撒切尔、里根、科尔上台,新自由主义权柄在握,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之流的新保守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优势。新保守主义者们最大的动力来自对“1960年代”的复仇。他们声称,当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源全在于激进的学生、黑人活动家以及强硬的女权主义者,而不是比如晚期资本主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回归传统,回归家庭,回归道德价值。不过,尽管左派在政治阵线上节节败退,在文化阵线上却颇有进展。当时五花八门的论战充满了活力,特别是批判理论,内容多样而混杂,英语世界尤其。为了消化这些新旧杂陈的观念,一大波评论杂志诞生了,包括《暗箱》(Camera Obscura)、《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变音符》(Diacritics)、《差异》(differences)、《新德国评论》(New German Critique)、《十月》(October)、《再现》(Representations)、《屏幕》(Screen)、《Semiotext(e)》、《社会文本》(Social Text)、《目的》(Telos)、《第三文本》(Third Text)、《楔》(Wedge)和《域》(Zone)。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无论当时的选项多么有限,从政治转移到批评都是桩不划算的买卖。当《社会文本》的一名编辑对我说,批评杂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党时,我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部分由于翻译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美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几乎是同时接触到法兰克福学派与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葛兰西经由英国文化研究和阿尔都塞、德波一起进入美国知识圈视野,而三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非常不同的路线。从索绪尔、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中汲取营养的法国女性主义和电影理论与福柯同步到来,而福柯对前三人的思想都持怀疑态度。《反美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分析这些不同的模型对当代艺术和建筑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这也决定了全书暧昧的立场:在对理论的投入上一马当先,在反对新保守-新自由主义秩序上却采取防守态度。但在有一点上《反美学》绝不含糊,那就是拒绝任何与新具象艺术和新装饰建筑相关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以风格为导向,比任何流派都更加反现代,而且似乎支持着反动联盟的文化政治。
此外,《反美学》也是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1979)出版以后问世的。利奥塔在他的书中指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精神辩证法,工人的解放,财富积累,阶级社会——最后都无疾而终。当时我想用一种反对的声音作为全书开篇,于是选择了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很巧,1981年,他在纽约大学发表了他的阿多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演讲“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新德国评论》于次年将该演讲全文刊出。文章题目已经说明了一切,哈贝马斯既不同意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里的意见,也不同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74)里的说法,他认为应该恢复现代对“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坚守。哈贝马斯承认,启蒙的目标——将知识划分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并以专业方式发展其各自的“内在逻辑”——最多也只是取得了好坏参半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导致这些活动远离公众。他也指出,“20世纪……粉碎了”人们关于“对日常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组织”的“乐观主义”愿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像达达和超现实主义那种“试图‘否定’专家文化的努力”大多是“毫无意义的实验”:“意义去掉升华或形式去掉结构以后啥都不剩;解放的效果并不会随之而来。”因此,他以提问的形式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是应该坚守启蒙的意图,尽管它们已经千疮百孔,还是应该宣布整个现代性事业都已经破产?”[1]
哈贝马斯对这种坚守的可能性并不乐观。他承认:“现代主义是显学,但它已经死了。其破产带来的幻灭感导致一部分人呼吁要否定艺术和哲学,这种呼声如今已成为保守立场的借口,”沟通理性也已经输给了资本主义理性。但他仍然号召我们继续战斗,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走向批判性地域主义:有关抵抗的建筑的六点考察》(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一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弗兰姆普敦看来,建筑是“本土文化”直面“普遍文明”的核心舞台。这一点转化了他借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提出的问题:“如何在成为现代人的同时回归本源,如何在唤醒沉睡的古老文明的同时也参与到普遍文明中去?”包括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丹尼丝·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罗伯特·斯坦恩(Robert A. M. Stern),以及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在内的后现代建筑师们提出了一种民粹式的“对历史的回归”,但结果“只是喂给这个媒体社会更多无谓且无为的图像。”[2]为了对抗这种犬儒路线,弗兰姆普敦要求建筑师们按照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原则来“(构建)场域”,并举出阿尔瓦尔·阿尔托(Alvar Aalto)和约恩·乌松(Jørn Utzon)的作品作为其典型例证。通过强调触觉和建构法,而不是图像和造景,建筑师也许可以推动一种感性的场所营造,以支撑起“人的现身”空间(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说法),从而抵抗晚期资本主义的侵袭。但是,很快事实证明,比起大众-历史风的后现代主义,那些被重塑为雕塑性媒体标志的建筑(以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为代表)才是更大的威胁,也更符合如今已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

再强调一遍,《反美学》倡导的是那些并非单纯反现代主义的实践。与此同时,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和道格拉斯·克林普(Douglas Crimp)在首发于《十月》杂志的文章里证明了现代主义有关媒介和博物馆的概念如何已深陷危机。克劳斯注意到,在极少主义出现后,雕塑这一范畴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在《扩展场域中的雕塑》(Sculpture in the Expanded Field)一文中,她重述了雕塑作为纪念碑的旧有定义,并在此基础上追溯了此逻辑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崩溃过程,先是在罗丹的作品中,雕塑进入了“它的负状态——一种无位置状态(sitelessness)”,接着在布朗库西的作品中,雕塑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标记物”,通过反思其物质材料和制作过程“描画出自身的独立性。”克劳斯认为,几十年来,现代主义者们在探索这一“唯心主义空间”(idealist space)上颇有建树,但慢慢地,这一空间“让人感觉越来越像纯粹的否定性”,雕塑在其中大多被理解为某种既非建筑亦非风景之物。然而,克劳斯用纯熟的结构主义手法指出,这一否定性的二元对立可以扩展到一个四元场域,雕塑在其中和“场地建构物”(site-construction)、“被标记场地”(marked sites)、“自明性结构”(axiomatic structures)三者一样,只占据了边缘四角中的一角。“在后现代主义状况下,”她最后的结论是,“决定实践的不再是某个给定的媒介——雕塑——而是对一系列文化含义的逻辑操作,就此而言,任何媒介——摄影、书籍、墙上的线条、镜子或雕塑本身——都可以用。”
这篇著名文章至今仍堪称是方法论的展示典范,在阐释模式上,它公开地强调结构多过历史,但正是这种强调导致其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保持了沉默,比如商品形式的优势地位以及景观社会的崛起,这些因素对雕塑产生的影响比任何逻辑操作都要大得多。[3]同样,其他批评家也纷纷启用克劳斯的四元场域,但他们所描绘的并不是艺术上的扩展,而是意识形态上的闭合。尽管大地艺术和其他类似的建构物的确从空间上扩展了雕塑领域,但在美学上,它们大多被证明是死胡同。[4]
如克林普在《在博物馆的废墟上》(On the Museum’s Ruins)一文中所分析的,历史的另一个狡计套中的是艺术机构。按照福柯的说法,马奈率先强调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自反性,从那以后“所有的画作都从属于绘画那四四方方、巨大的表面。”[5]那么,克林普问道,当摄影被放进这个表面,且不是作为单独的艺术媒介,而是如劳森伯格的作品所示,作为一种反灵光(anti-auratic)的图像复制和增殖的手段,情况又会如何呢?机构能够守住原来的学科界线吗?抑或这类后现代主义艺术彻底证明,如理论家尤金尼奧·多纳托(Eugenio Donato)所言,“博物馆展示的各类物件皆有系于如下虚构,即:这些物件不知为何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表象世界”?这场博物馆的认识论危机在当时看来非常重要,但放到今天似乎不值一提,尤其对比它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更不用提其背后掠夺和排斥的历史。

在《反美学》最具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他者的话语: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The Discourse of Others: Feminists and Postmodernism)一文中,克雷格·欧文斯(Craig Owens)把后现代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颠覆重述为一种“主宰力的丧失”。尽管“西方的再现系统只承认一种形象——本质上的男性主体形象”,但女性主义艺术家已经开始对这一支配地位发起挑战。由于长年“被再现的结构本身排除于再现之外”,女性主体成为其最敏锐的批评者,全力将其推向“毁灭”。因此,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首要招数就是“对挪用者进行征用”(expropriate the appropriator),欧文斯用如今已成经典的术语描述了这一方法如何在达拉·伯恩鲍姆(Dara Birnbaum)、珍妮·霍泽尔(Jenny Holzer)、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路易斯·劳勒(Louise Lawler)、雪莉·勒文(Sherrie Levine)、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和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等人的作品里发挥作用。最后,他总结道:“此处,我们来到了女性主义的父权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再现批判两者之间的交叉点。”欧文斯借罗斯勒之口提醒读者,女性不应成为“一切差异标识的象征物”;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性别不平等不能被简化为经济剥削的问题。”这种差异与总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今天有关种族和阶级的论战中大有强力回归之势。[6]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看来,任何差异只有通过这样的总体化操作才能被理解。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出版一年后,詹明信在惠特尼美术馆发表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这也是他关于该主题的第一篇文章。对詹明信而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系列既有元素的重新组合”,关于这一过程,他给出了若干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过去,知性的探索在各自独立的话语框架下进行,比如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文学批评,但如今,批判理论这一新产物穿梭于各个学科之间,自由取材于各处。接着,詹明信指出,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将两者对立,而后现代主义者喜欢将两者混合。更准确地说,现代主义者影射经典文本是为了戏仿(比如乔伊斯),而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把经典文本融入某种大杂烩,以削弱其规范性(比如凯西·阿克[Kathy Acker])。[7]最重要的是,詹明信拒绝任何从风格层面对后现代主义概念的理解。相反,后现代主义的目的在于“将文化中新涌现的形式特征与新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秩序”——即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互相关联起来”。如果说现代主义者们强调其作品整体的原创性,那么后现代主义者们上演的则是一场“作者之死”,他们的片段拼接法将现代主义中语言的碎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詹明信将其比作精神分裂的效果,“意义”在其中“已然消失”,“词语的物质性变得难以抑制”,世界“被转换成一张图像。”詹明信得出的结论是,通过搬演这种让人感觉高强度的“非真实性”,后现代主义表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真相”,即:对一切“历史感”的侵蚀。“我们的整个当代社会体系已经逐渐丧失了维护其自身过去的能力,我们开始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动里,之前所有社会形态以不同方式保存下来的传统在这里都被一一抹杀。”詹明信最后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生产——亦强化了——消费资本主义的逻辑;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里面是否也存在一种抵抗该逻辑的方式。”

在《交流的狂喜》(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把后现代主体比作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再也无法“为自身的存在划定界线”,“已经变成一面纯粹的屏幕,一个所有对他产生影响的网络汇聚的交换中心。”当然,和詹明信一样,这种给整个社会下病理诊断书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而鲍德里亚也的确喜欢发表极端言论,他的这种说话风格在1980年代的艺术圈不乏模仿者。但他提出了不少重要见解,其中一部分预见了如今我们身边的这种“仿真的超真实主义”(the hyperrealism of simulation)。下面引述几例:“跨入新维度的广告入侵了一切,而公共空间(街道、纪念碑、市场、现场)都消失不见了。”“身体运动”被“电子指令”所取代。“交流的即时性将我们之间的沟通矮化为一个个接连不断的瞬间。”“镜面和现场具有自反性的超越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反射的平面,一种操作不断展开的内在平面——交流平滑进行的操作界面。”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对立在“某种秽乱状态下被抹除了,在其中,就连我们生命中最私密的过程也变成了供媒体大快朵颐的虚拟饲养场。”
最后,在《敌手、观众、选民与社群》(Opponents, Audiences, Constituencies and Community)一文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对“阐释的政治学”的批判反思为《反美学》全书划上了句号。“阐释的政治学”这一短语体现了当时比较典型的一种话语加工:不是要再现或阐释政治,而是要将再现和阐释政治化。但萨义德已经警觉地意识到,这样的批评无论如何跨学科,都很难翻译为更直接的交流,传达给更广泛的观众。相反,“批评家们互相阅读,基本毫不关心其他。”如果一直以“技术性语言”为标准,以“自我管束”为准则,那么“人文学科的特殊使命”就将只是“在日常世界的事务中代表不干涉立场,”其主要功能也将只是“代表人文主义的边缘性,这同时意味着维持并掩盖(如果可能的话)占据中心位置,决定社会地貌并划定用途、功能、领域、边缘性等界线的权力等级秩序。”在像萨义德这样的人的指引下,人文学科在上述阵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代表“人文主义的边缘性”依然是其首要目的。

大部分稍微有点价值的文集都是紧迫性和偶然性的产物,《反美学》也不例外。这本书出版时,我二十八岁,是《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杂志的编辑和评论员,当时的我太想追踪文集供稿人所指出的那些艺术、理论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了。[8]紧迫性和偶然性带来了疏忽,其中一些疏忽至今仍让我倍感懊恼。尽管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都是女性,但文集作者里的女性只有一人,而全书唯一一篇关于女性主义艺术的文章出自一名男性之手。[9]尽管我参加过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讨班,但《反美学》里没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后殖民话语的。当然可以找借口——萨义德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和音乐,而不是艺术;像吉塔·卡普尔(Geeta Kapur)这样的批评家当时还没那么有名;像《第三文本》这样的期刊也还没有创刊——但借口只是借口。直到1984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声名狼藉的“原始主义”展引发争议,同时人类学内部开始自我批判,后殖民主义批评在艺术领域造成的诸多影响才开始显露。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所理解的差异还是更多指向了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他异性。
前文已经提到了自出版以来《反美学》触及的主题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此处我再补充几点,作为结语。首先,挪用的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在后现代主义实践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挪用的艺术”原本旨在挑战那些将作者身份视为权威,将艺术视为所有权的未经审视的预设。如今,这个概念却充满道德风险,“挪用”这个词也常常被用作一种指控。其次,尽管把后现代主义视作一种风格描述的想法一直是狭隘的,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时期划分标志的使用价值已经变得模棱两可。简言之,我们夸大了它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即便对于它和现代性(其宏大叙事在今天显得尤其失效)之间的距离说得不算太过头。当然,为后现代主义提供陪衬的现代主义是一种还原式现代主义,往往过于专注于某个假想敌或容易的目标(比如格林伯格或色域绘画)。也许,利奥塔、哈贝马斯以及其他人对现代性的定义也需要重新修订——后现代性亦是如此。第三,我在文集前言里指出有“抵抗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并将前者和后结构主义批评联系起来,将后者与新保守主义政治挂钩。文集出版一年后,我就已经对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产生了疑问,因为挪用艺术也好,后现代建筑也好,都可以被用来加速文化符号的碎片化,这比什么都更能体现资本的侵蚀作用。[10]
第四,对美学的拒斥有所缓和。当时,对于遍布周遭的懒惰的审美主义(后期的格林伯格主义、艺术摄影、新表现主义绘画、青铜雕塑),我们这帮艺术家和批评家都非常怀疑,对于作为一种范畴的美学同样如此,而数字革命刚刚开始,对于艺术的灵光,我们比本雅明(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还要排斥。作为不同机能之间的调和场所(如康德所定义的那样),审美似乎与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使得我进一步在抵抗的后现代主义内部划分出两种不同立场,一种葛兰西式的,一种阿多诺式的,并给出了我自己的最后通牒:
“美学的种种历险构成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一:从其独立开始,经过‘为艺术而艺术’,发展到其作为必要的否定范畴,成为对世界本身的批判。正是这最后一个阶段(被阿多诺写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割舍:在一个工具化的世界里,美学成为唯一具有颠覆性的批判缝隙。但如今,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一美学空间也已成为过去——或者说,现在它的批判性基本都是假的(从而也是工具化的)。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式的坚守否定性的策略可能必须得到修正或摈弃,一种(葛兰西式的)新的介入策略必须被发明。”
萨义德在谈阐释的政治学时也表示赞同葛兰西;而弗兰姆普敦、欧文斯和詹明信的文章都表现出反霸权的倾向;葛兰西式的立场似乎是在面对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秩序时应该采取的立场。然而,慢慢地,我开始怀疑葛兰西-阿多诺这组对立是否有必要。它们可能没有我当时出于紧迫感所描述的那么互相排斥。如今,对美学的坚持,甚至对“美”的回归重新出现,这在黑人艺术家和批评家中间尤其明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学提供了某种喘息空间,让我们能从对创伤性历史的必要关注中稍微脱离出来,看到“既定事实改头换面”[11]的希望。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批评的价值发生了转变,它不再像我们这帮人过去经常认为的那样代表无可争辩的好或不容侵犯的标准。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反美学》试图完成的那种批判性介入;后批评不是我的菜。我也不认为批评是修复性的;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接近于某种救赎性质的文化观,大部分最重要的艺术,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反对这样的观念。[12]批评和文化不是治疗,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
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野蛮美学:杜布菲,巴塔耶,乔恩,包洛奇,奥登伯格》(Brutal Aesthetics: Dubuffet, Bataille, Jorn, Paolozzi, Oldenburg)于202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
1. 除特别指出以外,本文所有引用均出自《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由哈尔·福斯特编辑(华盛顿州汤森港:Bay Press,1983)。谨以本文献给文集出版人,也是我的好朋友撒切尔·贝利(Thatcher Bailey),从文集开始构思到最后出版,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弗兰姆普敦的文章受到了一些建筑师朋友的质疑,他们认为批判性地域主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但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恰恰就是其批判态度;它指向了一种“抵抗的后现代主义。”
3. “雕塑的逻辑似乎与纪念碑的逻辑密不可分,”克劳斯在《扩展场域中的雕塑》一文中写道,“依照这一逻辑,雕塑就是一种具有纪念性质的再现。它栖身于一个具体的地点,以一种象征的语言诉说着该地点的意义或用途。”二十年以后,本杰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对这段话进行了一番有点恶毒的“再创作”:“雕塑的逻辑似乎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密不可分。依照这一逻辑,雕塑从开头就已经是一种物神化的对象,其功能在于否认。它缺乏任何具体位置,同时提供普遍的准入。它以一种象征的语言诉说着拜物教的意义或用途。”参见布赫洛的文章《雕塑:曝光与体验的贫困》,收录于《形式主义与历史性: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模式和方法》(Formalism and Historicity: Models and Methods in Twentieth-Century Art)(麻省剑桥:MIT Press,2015),第510页。
4. 参见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谈意义:符号学理论选集》(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由保罗·佩隆(Paul J. Perron)和弗兰克·柯林斯(Frank H. Collins)翻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同时参见詹明信撰写的前言。当然,最近有关“纪念碑的逻辑”的讨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
5. 米歇尔·福柯,《图书馆幻想曲》,收录于《语言,反-记忆,实践》(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由唐纳德·布沙尔(Donald F. Bouchard)和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翻译(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第92页。
6. 也可以说欧文斯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了总体化的处理,把所有权威都假定为支配关系。
7.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后现代主义文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与此相关的作家(比如约翰·巴思、唐纳德·巴塞尔姆、罗伯特·库佛、威廉姆·盖迪斯、托马斯·品钦,甚至包括阿米里·巴拉卡、威廉·巴勒斯)都更多是超级现代主义者。(此处,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的不同步值得我们反思。)在为《反美学》撰写的一篇关于“后-批评”的文章里,格雷戈里·乌尔默(Gregory Ulmer) 指出,在罗莎琳·克劳斯之后,批判理论自身已经获得了“准文学”的地位,这大部分是通过把现代主义对再现的批判,尤其是拼贴和蒙太奇等手法,带入到哲学领域而实现的。参见克劳斯,《后结构主义与“准文学”》,《十月》杂志第13期(1980年夏季刊),第36-40页。
8. 同样偶然的是我与文集作者刚好都熟识。我通过建筑与都市研究学会认识了弗兰姆普敦,通过《十月》认识了克劳斯和克林普。我跟欧文斯一起供职于《美国艺术》,和詹明信一起在《社会文本》工作。我在哥大跟着萨义德学习,在鲍德里亚访问纽约期间认识了他。
9. 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欧文斯的同性恋身份而有所缓和。然而,在欧文斯短暂的生命里——他于1990年过早地离世——他的确变成了酷儿理论的重要代言人,而在《反美学》出版时,这类理论才刚刚显露头角。
10. 参见我的文章《(后)现代论争》,收录于《重新编码:艺术,景观,文化政治》(Recodings: Art, Spectacle, Cultural Politics)(华盛顿州汤森港:Bay Press,1985),第121-138页。
11. 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恣意的生命,美丽的实验:社会动荡的私密史》(Wayward Lives, Beautiful Experiments: Intimate Histories of Social Upheaval,2019),第33页。同时参见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美是一种方法》,e-flux, no. 105(2019年12月)。
12. 此处参见我的文章《后-批评?》,收录于《来日非善》(Bad New Days)(伦敦:Verso,2015);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偏执型阅读与修复型阅读,或者,你的偏执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会以为这篇文章写的是你》,收录于《触碰感觉:情动,教学法,述行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123-151页;以及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救赎的文化》(The Culture of Redemption)(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文/ 哈尔·福斯特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