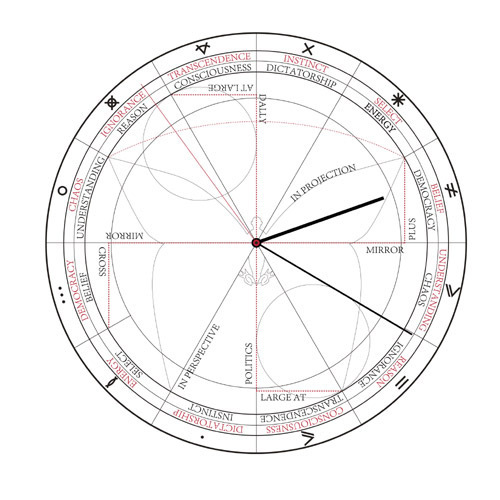曾建华
曾建华(Tsang Kin Wah)1976年生于广东汕头,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他的“图案绘画”(Pattern Painting)系列:墙纸上密集的花卉图案,细看方知组成花瓣花芯的是各种字词——包括脏话和色情电影关键词。《白色情》(White Porn)则是同样隐晦、不同程度的白在畫布上构成各种性虐待场面——如果说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式经典《白上白》(White on White)以提纯画面达到至上主义的升华,那么曾建华作品中虚虚实实的肉体就是以物质过渡到物质。基督教背景驱使曾建华将形而上学的叩问转向对神的质疑,艺术家理所当然地援引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多屏录像装置 《看!这个人!三部曲》(Ecco Homo Trilogy)题目源自尼采晚年书名,也是彼拉多向众人展示伤痕累累的耶稣所言,作品以罗马尼亚独裁者奇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广为流传的处决片段为起点,链接宗教和哲学层面上的观看和审判经验。《七封印》(Seven Seals)也漫溢着审判式末世论调。曾建华将在今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展出《无尽虚无》(The Infinite Nothing)——延续《看!这个人!三部曲》和《七封印》对神学、存在和死亡的思考。
我硕士修的是书艺(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