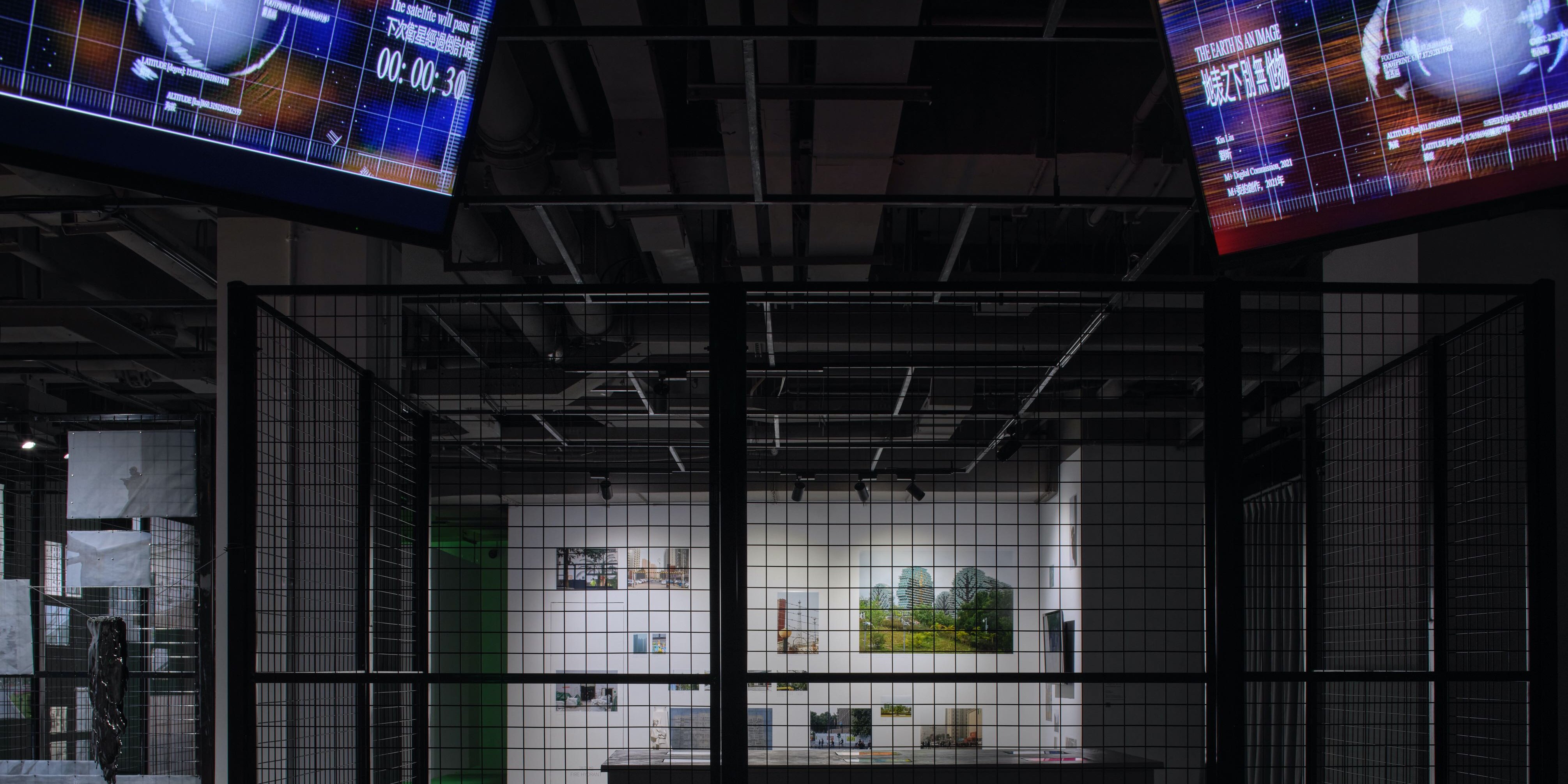金亚楠
金亚楠的展览从堆积在墙角的广玉兰枯叶开始。近万片树叶每片都被他用打火机灼烧了两个孔洞,宛如无数双荒诞又可怖的眼睛;它们沿着墙根铺陈开来,为方正的白色展厅勾勒出一道不规则的边界。此时的南京正值落叶乔木新陈代谢的迷人时节,逸空间所在的文创园和街边,同样遍布黄褐色的凋零痕迹。
走进异常高耸的主展厅,视线尽头处悬挂的网兜里包裹着孔雀羽毛,远看像一枚不稳定的秤砣或钟摆,诸多羽枝四散横斜,显得蓬松粗糙。《雀网》(本文提到的作品均创作于2025年)的下方,是形如头骨的筊杯切片(《头骨勘探》),铜箔经由不均匀硫化,在树脂表面沉淀出斑斓色泽,与雀羽的结构光色形成联动。羽毛用于候风以服务谶纬,筊杯用于问卜以预言命运,掌握对吉凶的解释权。这两种原本指向不可见之物的工具,在此被艺术家赋予了沉重的物质性——雀网轻重难辨,筊杯无法被抛掷,其表面更被雕刻出深邃的沟壑。它们不再承诺有效的观测和指引,反而让人不得不去重新凝视由于形制和材料的变化而显形的物质本身。
展厅中央,大屏幕播放着南京德基广场大理石地面的固定机位影像(《广场》)。在人来人往的脚步之下,一块螺旋状的菊石遗迹若隐若现。这一极富时空张力的场景,实际上在最喧嚣的消费核心区域日夜上演着:亿万年前的古生物残骸,正被当代纷至沓来的鞋底无意识地打磨。
金亚楠对这一场景的打捞,并非出于地质学意义上的对岩层构造的实证兴趣。文献区所展示的“调研”,乍看之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