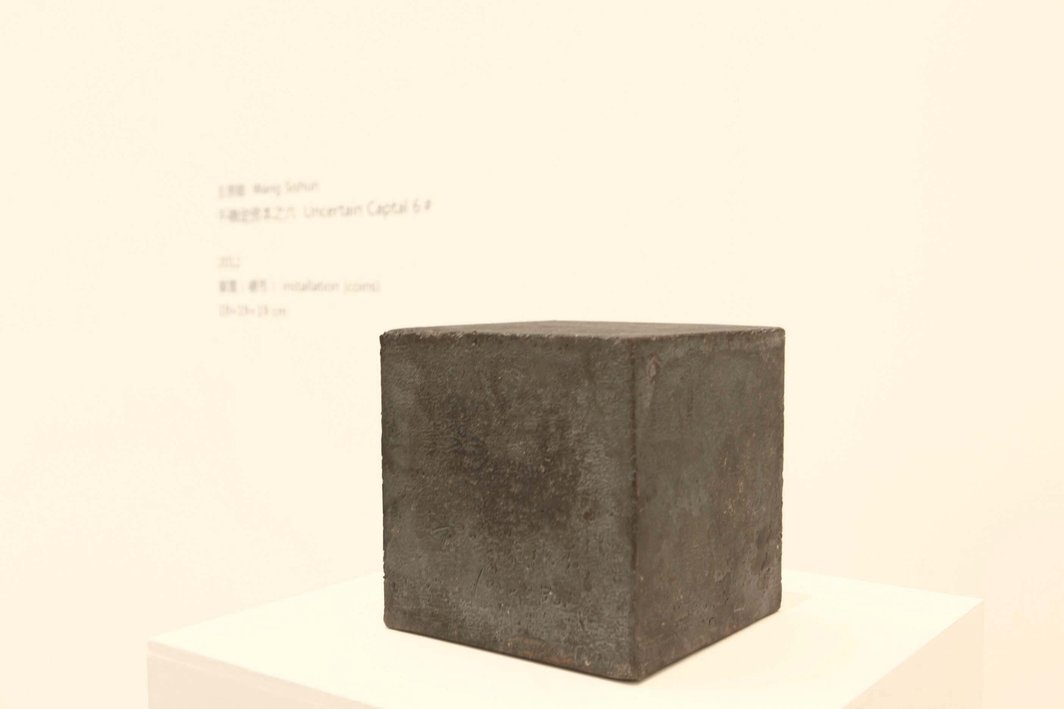“瓦尔堡的遗产”
围绕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所展开的研讨会的“所见所闻”是个不太容易下笔的题目,尤其当这两位学者的著作还尚未有中文出版的情况下,“所闻”很容易流于概念罗列或难以有的放矢。上交自己的会议笔记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既无法保证全面也难以保障忠实;而篇幅限制亦不允许任何逐一概括演讲内容的写作方案。类似的关于切入角度与深入范围的选择问题同样也是OCAT北京馆的学术总监和出版部主任董冰峰在策划该机构的第一场公共项目时所面临的挑战:在国内艺术领域第一次正式展开的围绕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研讨班究竟应该以“求全”的方式来迎补知识领域的空白,还是应当在开场即就其研究腹地的某些关键论题展开讨论?而在中文语境下,上述二选一方案中的任何一个亦存在如何切实保证广度和深度的问题。
董冰峰和他的团队给出了一个诚恳也更加合理的方案:将研讨会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的时间段内分为四期的系列形式,逐期展开围绕这位法国哲学家、艺术史学家代表性论著及策展实践的学术讨论。前两期面向提前预约的听众展开学科综述、专题研究和开放讨论,这样一方面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上聚集起中文语境下对于迪迪-于贝尔曼学术思想的兴趣人群和研究群体;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后期研讨的针对性和深入程度。2015年上中旬的后两场研讨会将邀请迪迪-于贝尔曼本人到场,意愿参与讨论的研究者可以在明年四月之前提交自己的相关研究论文(英法文皆可),由前者亲自筛选与会学者从而得以展开一对一的学术交流。